
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有人心里狠毒,写出的文字就阴冷。有人正在恋爱期,文字就灿烂。有人才气大,有人才气小,大才的文字如大山莽岭,小才的写得老实,讲究章法的是小盆景。大河从来不讲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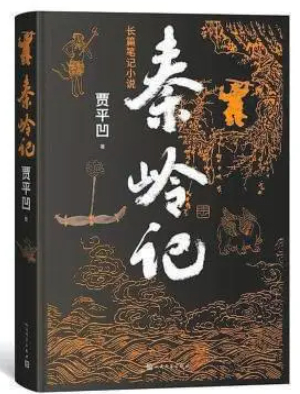
贾平凹的最新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开宗明义,将自然场景推到了叙事的台前,山川河流草木飞鸟走兽,成为小说文本的最大看点,而所有的人物隐身于自然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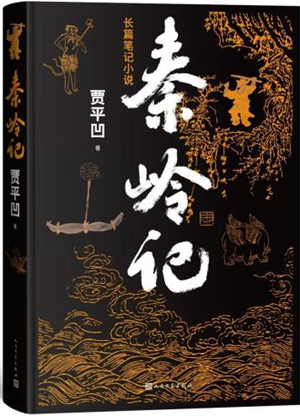
以秦岭自然山水和生活其间的草木鸟兽、自然天籁、生灵万物、芸芸众生为书写对象的《秦岭记》,是一部淋漓着秦岭本体文化意识和生命气象的秦岭精神之书、灵魂之书。

《秦岭记》所敞开的世界,属“阴”“阳”交汇,“天”“人”相应,“物”(动、植物)“我”共在的圆融会通之境。此境不同于现代以降之文化观念及其世界展开,乃是中国古典文化观念总体性面向重要一种的“境界的再生”,为由简单之“有序”到“浑沌”的表征,包含文化精神返归之浑融境界。

《秦岭记》的文学格局的气象依然宽瞻宏阔:古典与现代的互相凝望、时代和人心的重重激荡之间,作者所描绘的五光十色的故事画卷,犹如一幅山川胜景图缓缓展开。

《秦岭记》是贾平凹第一部以“秦岭”命名的作品,也是他的第19部长篇小说,再一次证明了“文坛劳模”这一称号实至名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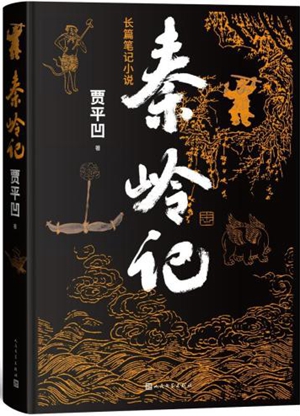
从《山本》到《秦岭记》,贾平凹承续了一以贯之的秦岭叙事。诸多评论围绕作家从长篇转向笔记,志人转向志怪,接续《山海经》《聊斋》以来浪漫传统等话题,展开探讨。然而,对作家“何以如此”的书写意图,却并未充分重视。我们需要重新“发现”贾平凹。秦岭不止是贾平凹醉心的主题,更深意义在于:秦岭,将作为视点和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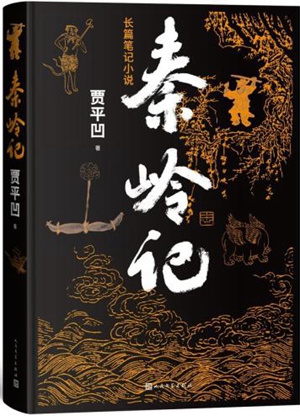
贾平凹在《秦岭记》题记中,郑重写下一行字: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这看似简单、朴素的一句白话,凝结蕴藏了作家对于写作、对于人生、对于秦岭、对于中国、对于人世间一切事物道理的情感、体悟和思识,用他自己的话说,《秦岭记》是他几十年生活经验、阅历、见识的厚积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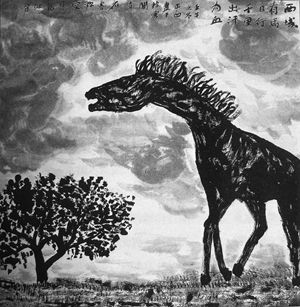
《秦岭记》主体内容五十七则,皆为短制,各有其貌,各显其形,如山如水如石如雾如云如风,混作一处,便显出秦岭的奇正、虚实,博大浩瀚、横无际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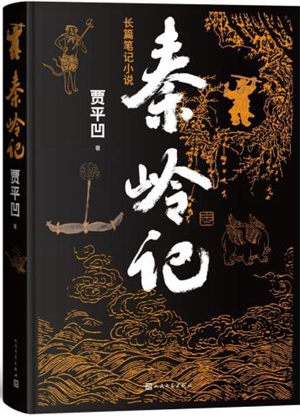
贾平凹重返生于斯、长于斯的秦岭,携带《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等传统古书中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基因,将秦岭里的物事、人事、史事娓娓道来,为读者奉献出一部在心里累积多年的秦岭山川草木志、动物志、村落志、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