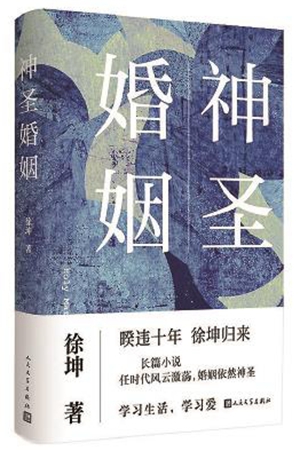
《神圣婚姻》,徐坤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小说创作,法国作家杜拉斯有个独特的观点:“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而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这个故事的那种空无所有。”徐坤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毫无例外地诠释了这一点。乍看故事写的是婚姻,深入品读后会发现,婚姻不过是作者用的“障眼法”:她以婚姻为单位探讨个体与城市进击、时代对话,以及沉积在日常中的时代嬗变,试图找寻到婚姻中恒定的东西。从布局、音调、细节、语言层面看,这部长篇力作具有开拓和创新的双重文本意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厨房》,到2008年出版的《八月狂想曲》,再到这部直面新时代现场的《神圣婚姻》,徐坤每回出场都给人以不同的新鲜感,怪不得作家王蒙称赞她“虽为女流,堪称大‘砍’”。然而,“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背后,是她身上特有的“野生动植物”气质。这种气质是对作家的一种高难度挑战,既要写得好看,又要不断出新,意味着技术和语言的双重突围。徐坤从不怵头,加速、转弯、跳跃、回旋,用速度覆盖空间,凸显人物内心剧变,她似乎样样在行。小说开篇写道:“许多年以后,程田田仍会清晰回忆起201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个晚上,她行色匆匆追到北京,就为听孙子洋亲口说一声结束他们之间的恋情。”既交代了女一号、男一号,也很好地点出了主题要旨,破碎的情感乃是人生悲剧的底色;同时,一个“追”字,把沈阳、铁岭、北京、澳洲等地关联起来。作者以一对年轻人的分手带出亲友圈子里形形色色的婚姻异变,看似写都市情感和心理矛盾,实际上是反映社会变革和时代向前历史漩涡下的精神困境。
婚姻是外衣,内核是人性。掩卷而思,小说内部设置极为讲究,上部为“市民的狂欢”,围绕于凤仙和孙耀第的婚变,下部为“精英的抉择”,聚焦萨志山和顾薇薇的婚变。凡俗与神圣之间的拉扯,字里行间埋藏着冲撞与对峙的角力、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从细节方面论,伴随人物的轮番出场和地点的腾挪转移,情节画面如临其境,给人以代入感和共鸣感,且注重前后呼应的完整性。比如,在顺义后沙峪顾薇薇家里,当律师的她向毛榛灌输恒价物的理念,“婚姻杀手可真是太隐蔽了,我要给婚姻和爱情这种变幻莫测的东西,找到对冲风险的恒价物。”谁能想到,丈夫萨志山为了逃避十年之痒,离婚后去了安岭挂职,工作中不幸牺牲,留下未婚妻吕蓓蓓和未亡人顾薇薇。几个月后,顾薇薇出席国际灯会项目剪彩仪式,虚拟的萨志山出现在大屏投影上,他生前的遗愿得以实现。这样的场景令人落泪,又深受感化。
正如樊梨花登门平息家事是事先写好剧本,从事编剧的徐坤更是深谙此道。她曾创作话剧《性情男女》,剧中的人物没有坏人,但存在各种问题,小说里的人物也是如此。她最高妙的地方在于把话剧思维有机融入小说里,“快闪”“留白”“移步换景”等运用的炉火纯青,剪裁恰到好处,避免拖沓乏味,语言急风骤雨,增强了审美张力和精神快感;另一方面,于纷繁变革中直击情感隐痛和社会阵痛,既有海归青年、北京外乡人、城市高知的生存困境,也有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支教、文化振兴等新时代火热现场,展现了体制改革语境下现代人的面临的复杂情境。这样就不难理解,“神圣婚姻”何谓神圣了,一来寓意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包容,才能使婚姻圣殿屹立不倒。正如毛榛离婚时把没有内页的红壳子结婚证带回家压在箱底,意味珍藏一份曾经的美好;二来指向生命个体的自我回归,在冲撞中修行,在痛苦中成长。作者借毛丹之口道出婚姻的真谛,“婚姻是什么?爱与背叛、别离相辅相成,时时发生。每个人还是过好自己最为重要。”
众语喧哗的网络时代,《神圣婚姻》是一贴“清醒贴”,也是一剂“强心针”。每一部长篇小说都会有作者的影子,因为切肤痛感,所以真实动人。结尾处,支教结束的程田田回到北京,与潘高峰相约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等待着那一神圣时刻”,从解构神圣到重构神圣,作者完成了自我的飞跃和圆满。这是致敬王蒙《青春万岁》里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何尝不是对现代人的爱情和婚姻深深祝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