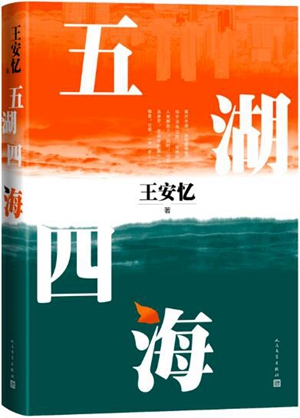
《五湖四海》,王安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王安忆的《大刘庄》中,上海人说走出去闯世界做生意的人“‘四海’得很”。对上海而言,“五湖四海”是众水汇流的海派都市文化,而王安忆的新作《五湖四海》则是一个从村庄深处内河,通达五湖四海的淮北水上人家的当代样本。
《五湖四海》,王安忆重访故地。无论是《五湖四海》工业园区选址地淮、浍、涡三河交汇之地,还是她《隐居的时代》写到的有一处分洪闸的县城:“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浍、淙、潼、沱五条河的交汇处,所以叫做五河。”其文学地理原型应该是王安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插队的安徽五河县。在《大刘庄》,上海知青和大刘庄离乡再返乡的百岁子一样的“搭一夜火车,到蚌埠;再搭一夜船,下了船,再走二十里地,就到大刘庄了”,这也是王安忆从上海去到大刘庄的路。
《五湖四海》略述三河河运简史。“自清中期始,黄河水枯改道,借此河口转入南北大运河,即成要道”,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往来还很繁忙。但因泥沙俱下,历年淤塞,行不得大船,渐渐式微。”可以作为参照的是,《隐居的时代》写到七十年代的县城码头上,叮叮当当的下锚和起锚的声音和走来走去的水手。那也是《五湖四海》张建设和修国妹们水上生活的最后繁华——“水上运输的黄金时代”。“沿河挤挤挨挨着大小码头,码头后面,新厂连老厂。……岸上是机器的隆隆声,岸下是船的马达和鸣笛。”“只听马达汽笛,此起彼伏,万舸争流的气象。”极盛,然后转衰。不能仅仅归咎于“历年淤塞”,而是路侵占了河,车取代了船。
王安忆《五湖四海》将张建设和修国妹的事业起点设置这盛极而衰、别出新路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仔细梳理王安忆的个人写作史,当她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青春期写作,首先给她赢得个人写作声誉的是“插队的故事”。《大刘庄》和《小鲍庄》都发表于一九八五年,这两部小说,尤其是后者,至今仍然作为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重要收获来谈论。假如认同王安忆的自述,小说中捞渣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小鲍庄》其实是在五四新文学启蒙谱系上的。几乎同时,王安忆“海上繁华梦”的上海往事也开始展开。这一条线索,以《长恨歌》为代表作,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上海书写的典范。其后,王安忆也自觉丰富自己的上海文学地标。但事实上,“插队的故事”一直是和上海往事并行的。《长恨歌》发表之后的第二年一直到新世纪之前,王安忆有《姊妹们》《蚌埠》《天仙配》《轮渡上》《隐居的时代》《喜宴》《开会》等中短篇小说相继面世。此际是王安忆个人写作史上的第二次重返故地。王安忆的上海不是沪港的双城记,而是城与乡的互看和互勘。以其上海往事论,王安忆的小说当然注意到现代殖民路线图的“上海摩登”,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上海之为现代上海,传统江南以及与上海有着密切地缘关系的苏北也参与了建构。
就王安忆个人精神史意义的启蒙和都市想象而言,需要加诸其中的是王安忆的插队往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安忆的寻根和文化反思,基本的观念和立场,和时风并无二致,但处身九十年代中后期上海的全球化和世界性在中国的最前沿,王安忆第二次重访故地,重写插队的故事,显然有其上海九十年代的问题意识。传统和现代的新旧之旧被赋予“理性化的审美观念”——“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形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慢流的自由的形态。”礼节严明,严肃,古板,守规矩,“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姊妹们》)王安忆这一时期插队的故事写“我们庄”的讲古、听戏、相亲、结婚、喜宴、开会等一日永恒的日常琐细,却时刻潜藏着可能性。乡土中国的可能性不只是在农耕生活之下的幽暗之地,也在农耕生活的边缘和末梢。这些边缘和末梢,比如流民、手艺人生活,比如《五湖四海》的水上生活,虽然在“安居乐业的农耕族眼里,漂泊无定所的生活,无疑是凄楚的”,但它却为改革开放自由经济来临,提前做好了准备。“集体制解体之后,就更自由了。”水上生活不仅开拓农耕文化的版图,而且水上世界也是一片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的水上生活从来就是农耕文化的矫正和补足,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苏童的《河岸》等等。
《五湖四海》并没有在这个文学传统上强调水上生活的独异性。就小说篇幅计,也只占八节中的两节多。在这两节多的篇幅中,重点也不在风俗史意义的水上生活描摹,而是张建设的水上创业史。张建设从头无片瓦、足无寸地的一条自家破船的“猫子”到五条船的船主,“日子过得快而且满,娶了娘子,生了儿子,攒了票子。”张建设对内河船运的没落是清醒而自知的,故而,《五湖四海》很难说是水上生活的挽歌。水上生活给予张建设的,重要的也不是原始的蛮性和野性等文学母题,更多的是自由——张建设是一个“走四方的后生”,是《大刘庄》里写到的“‘四海’得很”的人。正因为如此,《五湖四海》是张建设们这些“最后的水上人”到世界去的开拓史。在到世界去的路线图上,张建设从水上到岸上,从行船到拆船,最后公司如他期望顺长江东去,直抵上海崇明;修小弟、舟生到了更遥远的美国;当然也包括修小妹到南方。这些路线图是独立的、个人的,以一己之力开凿江河以“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确实可概括为小说所说的“激情四射的创业生涯”。小说的起点是张建设成人礼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十八岁那年,他从大队船上出来,单立门户。”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时代,也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青春期。“邓小平主政国事,政策松动,上头开一分,底下就是十寸。”张建设以沛然的激情拥抱激情的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张建设无疑是这几十年改革开放造就的时代新人和我们身边的时代英雄。
这种被时代改写命运的故事,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背景下展开的。如果要追溯《五湖四海》之张建设的当代文学起源,是新时期改革文学对乡村青年命运的关注。在这一条文学线索上,有我们熟悉的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等。《五湖四海》续写了乡村青年和改革开放时代等长的个人创业史。但是,《五湖四海》的创业史和成长史不是属于张建设一个人的,而是他和修国妹这个家庭族群的,这个家庭族群又接驳到更为庞大的社会网络。每个人都在开凿自己的人生河流,或清澈,或混沌,在他们各自湖海的河床入口。
需要指出的是,《五湖四海》张建设上岸拆船创业,也上岸筑屋买房。他给袁燕爸爸妈妈买房,给修小妹买房。“漂流的水上生活总是无根之萍。古代圣贤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他是个有恒心的人。和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反过来,意识决定存在,就是要用一颗恒心创造恒产。”张建设的创业史开拓了农耕文化的传统,但最终又为农耕文化所召唤所规约。缘此,《五湖四海》,似乎又遥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中国人命定的母题。而这恰恰是《五湖四海》之张建设一代乡村青年作为过渡时代的历史中间物的复杂和妥协。这些改革开放时代的长子们,他们亦新亦旧。
《五湖四海》最后意外事故终结了张建设的生命。这只是一个个案。更多的“张建设们”,他们活着,并且写下他们继续前行的生命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