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比作家思想中的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实际创作。每一个作家都会有个人的历史认知历史观点,存在一些局限,进入一些误区并不奇怪,事实上也很难避免。然而,进入创作后,作家忠于生活,按现实本来的面目去描写,去表现,尊重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讲故事,写人物,通常都会弥补作家思想的局限性,帮助作家走出思想的误区。优秀的作品,都会有这样神奇的突破调整的功能。历史上不少伟大的作品,都是在这个自我修复、自我调整、自我再生的创造过程中,实现思想艺术的突破和创新。我们常说的作品大于作家,形象大于思想的道理,说的就是这个艺术规律。《家山》将再次实证这个规律。
关键词:《家山》 历史观 人物形象 文化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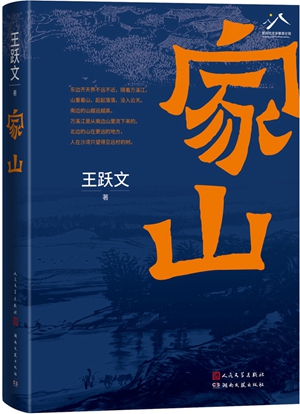
《家山》,王跃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家王跃文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引发了高度的社会关注,最新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家山》则更多受到评论家们的热情赞扬。在不久前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作家“将自己蓄积已久的创作力来了一次总爆发”,作品“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乡土中国的长卷”,表达了“出于善而得到和”的主题思想。尽管这种研讨会式的评论还显得有些任意,但却清楚地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可能正在迎接一部重要的小说作品。
长篇小说《家山》以湖南接近西部一座叫沙湾的乡村两个陈姓耕读人家的家族生活故事为主体,反映了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乡村的历史风云,描写了水深火热的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考察了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困境,美好的人性所面临的时代性考验等现象,从而展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的传统乡村社会的变化和中国农民的生存斗争精神,揭示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基本规律。当代中国家族小说的时间跨度一般都要超过百年,经历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品主人公不断交替,而《家山》则有意把时间跨度控制在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二十多年里。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社会矛盾冲突最复杂最激烈的动荡时期,佑德公(陈修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乡绅,儿子陈齐美(劭夫)从军在外,女儿陈贞一也外出读书。这个家族在沙湾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另一个耕读之家以陈远逸为家长,六个儿子,人丁兴旺。其中老大在国民政府高层做官,三公子陈扬卿留学日本,回归乡里。由于这两个家族恪守传统,敬畏孔孟,知书达礼,行善积德,和陸相处,多少年来一直引领着乡村风尚,使这个处于风雨飘摇时代的小村子一直过着平安祥和的生活,成为远近闻名的仁义之村。然而,这二十多年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打破了乡村宁静生活,改变了沙湾村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沙湾村的历史走向。
第一件大事是刘桃香家的男人陈修权(四跛子)在一次与邻村的械斗中,失手杀了自己的外甥,引发了官司。主事的农会主任陈扬高乡里横,上不了台面。女人刘桃香被迫出面,为自己的男人辩护,打赢了官司。刘桃香出了名,被尊为“乡约老爷”,但沙湾乡却很没有面子。那么多读书人,却让一个弱女子出来担事。最后是桃香生了儿子,过继给四跛子的姐姐,才算平息了两家的仇恨。主人公佑德公并不认为是偶然,而认为是两个村子五百年来利益之争(田水之争)的延伸。所以他拼命消除化解两个村子之间的世仇,但事情本身却揭开了沙湾村打破平静生活的序幕。
第二件大事是县长李明达为解决财政难题,一改过往的“减租减息”,推行“赋从租出”的税制改革。这个想法李明达县长最初曾与佑德公讨论过。出于对沙湾田家与佃家真实关系的考虑,佑德公提出“赋从租出”的核心内容。思路没有问题,但施行起来却遭到了农民们的强烈抵制。政府本来就是想利用税收向百姓那里多拿钱来补贴财政,所以借着税制改革,不断出台繁多的税种,农家苦不堪言。农家受不了,不得不纷纷抗租,乡绅们也向省里状告县长。税制改革走向了反面,不得不随着李明达调离自动流产。正人君子的佑德公也有苦难说,有口难辩。这件事不光是佑德公受委屈,实际上已经触及传统乡村的基本经济关系,揭示出深刻矛盾。
第三件大事是佑德公的小女儿贞一给新来的县长朱显奇写信提倡放足。县长很重视,举办了解放妇女缠足的盛大现场会,一些妇女当众放脚。沙湾桃香的五岁女儿月桂也作为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参会,县长把她变形的小脚举起来示众,并亲自给她洗脚,引得桃香跑到县政府门口大骂县长找的是婊子们来放脚。事情办得有点走板,但社会效果还是好的。妇女们因害怕再被叫去洗脚,也就不再缠足了。对沙湾村来说,这件事加速了办教育的进程。在回乡潜伏的共产党员陈齐峰和军人陈劭夫以及乡绅们的支持下,祠堂挂起了“沙湾陈氏国民初级小学校”的牌子,村长陈修根担任校长,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扬卿当老师。缠足又放足的月桂长大后,脚越发难看,后来被夫家休回娘家,不得不选择出家当尼姑。
第四件大事是红军在沙湾住了三天,指挥部设在佑德公家。村里连同佑德公家的长工共十二人参加红军。红军走后,新来的县长吴放贴出布告,捉拿共党头目周介民。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剿杀红军家属。齐峰来报信,佑德公紧急安排村里所有“红属”连夜进山,躲过血腥的大屠杀,但还是有两人来不及走,被烧死在屋里。几天里,全县有两百七十多名“红属”惨遭杀害。沙湾村损失最小。
第五件大事是进入抗日战争以后,村里一批青年以在前线带兵作战的劭夫为榜样,自愿参军。征兵是个大难题,逃兵役的现象十分严重。县里不断安排下的名额越来越多,让保长陈扬高非常头疼。同时,他又欺负朱家势力弱,想让小学老师朱克文去当壮丁。壮丁之事为一向游手好闲的五疤子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他提出朱家出十石谷米,他就可以替朱克文当壮丁。虽然是征兵的舞弊犯法行为,却解了乡长向远丰和保长陈扬高之围。五疤子过几天就从部队里开小差跑回来,继续干着替人当壮丁的勾当,不过,谷米涨到十二石。劭夫战场受伤,回家养病,荣归故里,成为英雄,起到榜样的作用。村里一批青年深受教育,懂得保家卫国的意义,自愿走向抗日前线。五疤子也有所觉悟,要求跟着劭夫杀敌,终成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第六件大事是陈扬卿设计多年的红花溪水库终于开工建成,为整个地区增加上万亩好田,老百姓的贫困生活得到了缓解。然而,政府乘机巧立名目,又增加了新的税种,直接就剥夺了老百姓因水库建成带来的好处,好事变成了坏事。正赶上一次重大的洪灾,包括沙湾村在内的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政府因打内战的需要,不管老百姓死活,不减税赋,强逼老百姓,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税暴动,佑德公成为沙湾村抗税斗争的领头人。
第七件大事是两年前就率部起义的劭夫回到沙湾,和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周介民(陈齐峰)、史瑞萍,以及进步人士、警察局长朱克文等人会合,成立人民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沙湾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还可以讲出不少事情来。实际上,《家山》大量的篇幅,是在描写乡村的风土人情,写老百姓平淡无奇、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由农事活动、家长里短、油盐酱醋、民风民俗构成的乡村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也构成所谓的“乡土中国长卷”的血肉。这些大事像筋骨一般穿插分布其间,形成乡村历史的一些重要结点,让人看明平静的乡土深处的历史运动的热流,也可以形成生活的亮点与光彩,让人感受着乡村历史的特殊魅力,碰撞出一部悲壮而又激动人心的乡村史诗。
读《家山》不用特别用心,就一定会注意到,作品下大力气讲述佑德公家和陈远逸家的故事,确实有一个“出于善而得到和”的思想前提,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沙湾乡人顽强地保持着传统道德,坚持着自己的日常生活理念,守望着乡村的风俗人情,虽然有些不识时务,也有些自不量力,但这种抗拒精神却衬托出传统文化的力量,显现出乡村之善、乡村之和、乡村之美。作家对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乡村史以及历史的演进有着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历史认知,形成更倾向更接近深受孔孟等传统思想影响的、以“善”为核的文学的历史观点,突出作品的思想主题。
把“善恶”关系转化为一种文学的历史观,通常被表述为“人性论”,在当代家族小说创作中相当普遍。这种文学历史观曾经一度很流行,并在改革开放时代再度流行,成为一个时期文学思想的优势,也暴露出这个时期文学思想的局限。过度迷恋“人性论”容易进入思想的误区。历史进程的规律本身不能简单用“善恶”道德来描述,但文学讲述故事描写人物通常会有“善恶”之分。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建立什么样的历史观,是目前文学创作思想的纠结所在。
其实,比作家思想中的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实际创作。每一个作家都会有个人的历史认知历史观点,存在一些局限,进入一些误区。然而,进入创作后,作家忠实于生活,按现实本来的面目去描写去表现,尊重艺术规律进行创作,讲故事,写人物,通常都会弥补作家思想的局限性,帮助作家走出思想的误区。优秀的作品,都会有这样神奇的调整突破的功能。我们常说的作品大于作家,形象大于思想的道理,说的就是这个基本的规律。《家山》将再次实证这个规律。
作者本意要写这两个耕读人家,仁义人家,打底的就是“善良”与“和谐”的故事和人物思想基调,描写的就是美好的人性,讲述的就是一个仁义的村庄人们和谐共生的日子。而我们读到的,除了作家要告诉我们这些内容外,还发现,沙湾村美好的人性道德,传统文化与带有强烈冲击性破坏性改造性的先进思想和社会革命之间,特别是当时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之间,不仅没有像许许多多小说那样,矛盾冲突,势不两立,不可调和,反而能和谐统一地融为一体。或者说,作品成功地让传统的文化融进了一个革命的时代,成为先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发展。而这些具有创新意识的内容,远远超过作家想告诉我们的本意,很可能作家创作之前也没有预料到。正是冲突而又和谐的关系的存在,沙湾村古老的传统文化,才闪烁着新的时代光彩。
作品是怎样摆脱历史的局限,怎样把思想误区变为思想的高地?在提炼出来的沙湾村大事纪里,就可以找到重要的线索,那就是作品对乡村田家与佃农之间关系的深刻揭示。几乎所有讲述传统乡村故事的乡土小说,更看重的是乡村的宗法制度和宗法关系。这些作品把乡村的密码寄托在文化关系的破解上,而《家山》则更看重乡村的真实存在的土地租赁关系、分配关系、税赋关系的揭示。从这些基本的民生入手,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去破解乡村文化密码,写出真实的传统乡村。新的发现令作品出现意想不到的思想格局的调整、思想深度的调整,从而使作品转换到新的视角,产生新的思想主题。这是作品描写乡村揭示乡村关系的独特之处,也是这部作品比其他家族小说写得更深的独到之处,更是作品超越作家个人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思想局限的独特之处。
作家笔下的沙湾村佑德公家祖上最多时候有五千亩地,到他这辈只剩下三百多亩。因为独生子劭夫从军在外,他一个人的能力只能种八十亩,忙时还要请工。其他的土地就租给其他人,其中有一百多亩租给了村农会主任陈扬高。他们家兄弟多,自己家田产少,只能靠租别人地种。沙湾村几百年不变的田家与佃家的经济关系一般都是五五分。佃家只交租,不向政府完赋。政府税赋全由田家负责。时间长了,五五分成并没有那么严格执行,但政府的赋税一点也不能少。按佑德公给县长算的账,陈扬高家租他家的地,已有五十年之久。久佃成业,这一百多亩地差不多就是陈扬高家的了,赋税却一直由佑德公家交。这样一来,佃家比田家合算,实际日子过得比田家好。在一些地方,出现地主变成佃家,佃家变成地主的情况,好像风水轮流转。所以佑德公主张赋从租出。田家可以减租,佃家完田赋。当然,在那个税赋层出不穷,变着法子出的年代,再好的税赋主意,最后都会变成更重的税赋压在农民头上。
作品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个现实,显然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沙湾社会复杂的特殊的经济关系,并非简单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也并非用一般的阶级斗争理念就可以揭示这些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的内涵。沙湾村的乡村关系比阶级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当外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沙湾这个地方却没有搞起来。沙湾的乡绅佑德公这样的田主,自己也是劳动者,更像真正的农民。而像陈扬高这样的佃农,在村子里争取到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会玩一些权术,在乡里呼风唤雨,日子也比别人好过,看上去更有田家的派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有可能倒过来。事实上,陈扬高很多时候比佑德公更像地主,更像土豪劣绅。因此,在佑德公这样的人身上,反而更加体现农民的质朴、农民的艰难、农民的革命性。沙湾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并不掌握在乡绅佑德公手里,而是掌握在日子过得比乡绅还要好的陈扬高手里。这样特殊的阶级关系,必然大大消解了阶级斗争的力度。因此,沙湾村尽管知道外面连县长等官员都被杀死了,也没有掀起农民运动的风暴,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沙湾村在大革命时代,保全了“仁义村”的完整,避免了沙湾社会的动荡。
了解沙湾村的乡村基本关系后,就能理解作家思想的倾向性,也能读出《家山》基于沙湾村的现实,找到了一个摆脱阶级斗争模式来描写中国乡村历史、中国农民历史的文学表现的入径方式。这个方式可能还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却也打开了作品的叙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空间。
《家山》的主人公佑德公并不是沙湾村最有权势之人,还不算强旺家族,却是最受人尊敬的乡村智者。六七十岁了,仍然每天都在田间劳作,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农民。敬神尊祖,仁义做人,规矩做事,厚道待人。他每年都按政府的要求,自己早早就纳完税赋,还积极动员乡里人依法纳税。沙湾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村”。村里遇到大事难事时,村长陈修根和农会主任陈扬高都会来听听佑德公的意见。他们两人虽然掌管着村里的大小事务,但只有听到他发话,心里才能踏实。佑德公其实就是宗法制度的维护者,也是沙湾村的压舱石。
如果仔细读《家山》,就能发现佑德公其实一直忧心忡忡,如履薄冰。桃香的老公四跛子,因与邻村械斗,失手打死了外甥,佑德公紧张得不行,连夜在祠堂开会,商量怎样平息。春节,村里办例行的游街,也要偷偷到邻村通报,生怕引起误会。陈远逸家房间多,借给叔伯兄弟陈远达家住,时间长了两家发生矛盾,本无佑德公什么事,他也要前去关心,调停纠纷。他心里知道,自推翻满清以来的世道,就一直非常动荡,沙湾村这种传统的乡村,根本无力抗衡外界的冲击。特别是农民运动的烈火,离沙湾村越来越近。他从陈扬高蠢蠢欲动的表现中,感觉到这股热浪正在逼来。所以,村子里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内心的不安和恐慌,都要想办法平息,防止事态的扩大。越怕事越出事。县长李明达找他商量农民税赋改革问题。他觉得这个县长想干点事,问题也提到点上,就如实地谈了自己的“赋从租出”想法。不料,这些想法一经政府实施,就走了样,佃家不满,田家也不满,最后引发了乡绅联名告李县长,还把火烧到佑德公身上,说是他出的主意。佑德公无法辩解,内心则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腐败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形势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红军来沙湾村住佑德公家,他看天太冷,让人送点炭过去,结果红军回他一个光洋。红军走后,白色恐怖接踵而至。共产党员陈齐峰急切找到佑德公,说新来的县长吴放正在阴谋追杀“红属”,村子里有十二个青年跟着红军走了,他们的家里人面临危险。佑德公马上安排他信得过的好人陈有喜,将五十多名“红属”带进山避难。然后,他专门找了当上保长的陈扬高,交代他守住道德底线,不许出卖乡亲。陈扬高虽然刚参加了国民党,但关键时刻仍然分得清是非。很快,其他村子的“红属”惨遭杀害,而沙湾村因为有佑德公,损失最小。这件事情对佑德公触动很大,他深知:自己和沙湾村的命运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裹挟着,进入了一条他无法掌控的历史轨道。
好在他有着朴素而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儿子陈劭夫,也认为儿子的几个朋友陈扬卿、陈齐峰是好人,是一些可依赖的人。儿子从抗日前线回乡养伤,给他带回许多外界的信息,让他大开眼界;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激活了他内心的家国情怀,看到民族解放的前途和力量。他虽然对国民党的抓壮丁和各种舞弊深恶痛绝,却仍然以大局为重,动员村里有为青年参军抗日。同时还组织支持和鼓励村里的农户,把余粮捐献出来送给前线。他从为村里人做好事,慢慢发展到为国家、为民族做好事——善良本性加入了国家民族大义。佑德公的觉悟转向革命转变,是在沙湾村遇到特大洪灾之后。灾年农民严重歉收,许多人家日子都过不去,政府不但不赈灾,反而不断加税,引发了新一轮的抗税浪潮。征收处的人专门来请佑德公这个纳税模范现身说法,带头完税。佑德公说出了他内心:“我带头抗欠。”由此,他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个人物形象的挺立,真实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传统乡村农民从保护旧文化到接受新思想到参与中国革命的曲折而必然的过程,展现了中国革命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农民身上有太多太重传统的负担,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在现实斗争中,一点一滴卸下负担,一点一滴地孕育积累起来的。正是时代矛盾冲突最剧烈的时候,农民的斗争精神才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作品通过佑德公这个人物,也表明,革命可以不必意味着以传统文化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传统文化经受着时代的考验,证明可以助力新的时代,也可以融入新的时代思想结构里,这是佑德公这个人物形象大于作家思想之处。
沙湾村另一个大户的儿子陈扬卿这个形象则是生动代表着一种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他刚回乡那阵,与乡村文化并不和谐。农民们都穿草鞋,他穿皮鞋。他喜欢人家叫他陈老师,以示自己西式的优越感。他努力为村子里办教育,却在相当长时间里,找不到与村民更融洽的沟通方式。有一次,他看到武汉来的史瑞萍把草鞋当鞋套,走过泥地进屋前脱下,保持了鞋子的干净。这个细节,不仅使他爱上了史瑞萍,也找到一条与农民沟通情感的途径——学会穿草鞋。他虽然清高,却也有士为知己而死的侠气。县长李明达离职前的那个雪夜,交代他要造福百姓就是兴水利。从此,在日本学水利的他一直记在心里,一个人自费进行多年田野调查,走遍全县山水,规划水利线路,找到建水库的最佳位置,写出了一份详实的专业报告。经过多年的坚持,他的报告得到政府批准,水库得以建成,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作品花了较多笔墨去写他设计水库的过程,突出他的专业能力,更突出他深入严酷的现实,接触真正的民情,感情发生了变化,政治意识也得以提高,开始同情共产党人,特别是在共产党员史瑞萍的引导下,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这个人物与佑德公形象异曲同工,相映成辉,展现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进步文化在乡村历史的互补进步作用。
中国自己的先进思想由陈齐峰、陈劭夫、史瑞萍等共产党人共同传播,引导着沙湾村朝着历史的正确方向变化演进。在村里人看来,陈齐峰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他的公开职业是乡村小学教员,其实见多识广,朋友很多,整天忙得家也不回,老婆孩子也无法管,家里对他很不满意。只有佑德公一个知道他的真正身份,知道他在干着大事情。他最信任的人,还是佑德公,他们共同完成了转移五十多位“红属”的任务。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党的领导,也是政府通缉的共党要犯周介民。
陈劭夫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将领,带兵在抗日前线英勇作战,其实,他早年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受党的委派,常年潜伏,等待时机。他爱上了大家闺秀朱容秀,却在大婚的日子回不来,家里人只好请一只生机勃勃的大公鸡扮新郞,与新娘拜堂。他动员妹妹陈贞一到长沙读书,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女性,嫁给了同样潜伏在军队里的共产党员郭书坤。郭书坤牺牲在台湾,陈贞一被迫滞留在那里,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回沙湾故乡定居。小说正是巧妙以陈贞一的现在视角,讲述着沙湾的历史故事,所以很合理地只讲到新中国诞生之前。
作品描写共产党人的手法较为简约,如写史瑞萍,写得较多的是她与陈扬卿恋爱生子,成为沙湾村普通的女人。她做的最光彩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唱现代歌曲和西方音乐,带进新的文化,很少看到她直接参与革命行动。不过,在作品的叙述过程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共产党员们的身影,感觉他们时时存在。作品中的共产党员以及进步人士的形象,除了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之外,他们都尊重传统的乡村文化,作品想通过他们传递出一个思考:革命不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而是把传统文化建构成跟上时代的新文化的建设者。
作品塑造人物形象时,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小说一开头,就写桃香充当“乡约老爷”角色,为自身的权益敢跟政府打官司,个性非常突出。可惜,作品后来更多写她与女儿月桂的关系,放弃了让她对社会生活的更多参与。
《家山》还延伸出几个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进一步讨论。一是作品显然受到《白鹿原》的影响。《白鹿原》写的是白鹿两个家族之争产生的复杂冲突关系,而《家山》则写的是两个家族的和谐相处。前者的历史观被小说中的智者朱先生表述为“鏊子论”,也给作品带来一些争议。这种朴素的乡村历史观,上升为文学的历史观就会加大负面的因素。不过,这是改革开放反思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困惑与迷茫。而后者与当代和谐和平的历史观有更多的联系,反映了当前的社会和解沟通对话的文化思潮,突出了国家民族的共同命运、共同理想。
二是作品的现实问题意识。作品写的是旧中国的故事,农民问题在当时是个突出问题,不过,今天的时代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例如,作品重点描写农民长期无法摆脱贫困,农村长期无法得到振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沉重的税赋。旧中国根本无力破解这个难题,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积累了丰盈的社会财富,才可能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通过农业税的取消,有力推动乡村摆脱贫困、振兴发展。作品抓住这条线索贯穿整个故事,用心良苦。
三是作品有自己鲜明的问题导向,意味着作品虽然带有浓重的乡土生活气息,却仍然属于农村题材小说,而不是近年来流行的那种乡土小说、新乡土小说。从新中国文学建构起来的农村题材创作,直至改革开放后,对准的正是“三农”实际问题。这种小说可以写得很接近“乡土”,骨子里却很“农村”。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乡土小说对准的是知识分子的内心,强调的是人性批判,乡土是知识分子内心的田园,并非真实的农村。这类小说无论怎样“农村”,骨子里都在表现自己的“乡土”。相对而言,写“乡土”容易,写“农村”难。《家山》选择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