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的沙湾村,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动荡中,进来两股新的理性力量,它们冲击着原有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结构。一股理性力量是以留日知识分子扬卿为代表的新知识、新技术;另一股理性力量是以共产党员齐峰为代表的新观念、新制度。两股力量合力推进沙湾的改变。在不合常理的地租、赋税、徭役、杂捐的无休止折腾中,温柔敦厚的沙湾人也表现出激进的一面。这两种力量的结构也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形,沙湾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完成蜕变的,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形象饱满的人物,诗意化结构对人物塑造是一种挑战,小说刻意不突出人物戏剧化的人生,而是通过平凡普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塑造人物。
关键词:王跃文《家山》 人物塑造 理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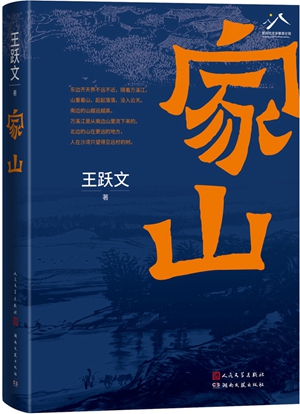
《家山》,王跃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家山》的冲突与和解不是建立在沙湾村内部,而是建立在每个人自身,以及每个人与沙湾外部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沙湾有完整的家谱体系,人们在这个体系中位置很清晰,以严密的人伦关系为底层逻辑,各种类型的人物成长过程都以沙湾人的视角展开,仁、义、礼、智、信的评价标准始终是有效的。千百年来,沙湾人随着历史的步伐,被既定的制度推动着前行,从未想过作出选择,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的权利。沙湾的男人们的责任和梦想就是在家谱中留下一个名字,死后在祠堂留下一个牌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享受人生,将有限的个人权限发挥到极大。《家山》中沙湾地处南方丘陵地带冲积平原,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沙湾人整体看起来过着诗意田园般的生活,整部小说弥漫着优雅散淡的氛围,作家也有意用田园美学掩盖某种真相。1927—1949年正是中国从封建王朝转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节点上,也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最为动荡的年代,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沙湾村人也不得不卷入时代的巨大动荡之中,不得不脱离原先的位置重新定义人生。在《家山》中,作家用心塑造了扬卿、佑德公、齐峰、有喜、桃香、一贞、史瑞萍、劭夫等众多人物。作家撇开外貌勾画,通过人物言行、内心世界、外部评价,形成饱满生动的形象,反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典型性与历史性意义。
一、两种理性力量的构成
祠堂、家谱的权威性和象征性贯穿了整个《家山》小说,它们代表着某种秩序的力量。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祠堂是宗族与国家连接的中介,宗族意识形态通过祠堂这个渠道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而家谱则是较为系统地记录“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祠堂与族谱皆为地方族群的精神性象征。家族男性长辈掌握着传统道德人伦的解释权,沙湾人凭借着这种精神象征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道德伦理的约束力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法律的力量,其中的合理成分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系中仍然有威慑力。沙湾村是一个富庶的村庄,更有能力建设他们的道德体系。时间来到了20世纪上半叶,有两股新的理性力量冲击着原有的体系,一股力量是新知识、新技术,以扬卿为代表;一股力量是新观念、新制度,以齐峰为代表。史瑞萍是两股力量的粘合剂,使之合力推进沙湾的改变,最后,新观念、新制度掌握了主动权,形成不可逆的发展势头。
小说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就交代了沙湾人族群的内部关系,“沙湾陈家自祖公老儿起,分作五房。敬远公是满房头,至今班辈高。放公老儿同修权屋里是四房头的满房,班辈也高”。小说的扉页插入家谱图表,也使得人物的辈份一目了然。扬卿是《家山》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扬字辈,比佑德公(陈修福)辈份高。齐峰也是主要人物之一,他是齐字辈,比扬卿低两辈,按辈份该叫扬卿公公(爷爷)。“敬远公手上第三回修家谱,派字往上数五代,往下排到三十二代,叫作:福贵昌隆,家声远扬;修齐有本,锡庆延长;怀祖崇善,世代辉煌;威振华汉,烜耀东方。敬远公是声字辈。发脉发派到今日,沙湾最高的是逸字辈,最小的是本字辈。”沙湾陈家辈份严整,朱家却独此一姓,沙湾村朱家和隔壁舒家村舒家才是原住民,两家“明朝手上是结拜兄弟,一起承头修青龙坝。沙湾朱家慢慢败了,陈家兴旺了。陈家最早也是朱家郎婿”。也就是说陈家与朱家也是由姻亲关系发展而来,尽管两家有怨恨,陈修岳与朱银翠的联姻再次证明两家牢固的亲戚关系,因此,整个沙湾人伦关系是清晰的。
佑德公是旧式文明的代表,他是这个体系的历史参照。扬卿利用知识确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他要凭一己之力将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新技术回馈于沙湾村。他兴修水利,办新学,教育乡民,爱家乡,爱人民。他想让乡民们以新知识新技术与世界打交道,以不同于过去的方法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经过扬卿的引导,沙湾人打开了视野,主动地、自觉地产生对新世界的追求。有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齐峰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有广阔见识和坚定信仰,看清了社会结构和所有人的处境,与当时的同道者一起要冲决这一道封闭的闸门。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一项不被沙湾人理解的事业。他的悲壮不同于旧时武士舍身取义、儒生杀身成仁,他带领沙湾青年追求终极人文关怀:明理和觉醒,以一个当时看不到希望的名为“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带领人们寻求彻底的解放。扬卿和齐峰并没有形成道路之争,他们最后汇合成一股力量。从文本中可以看出,扬卿通过技术和知识的传授,获得沙湾人广泛的尊重。而齐峰的道路异常地艰难和崎岖,被喊作赤匪首领的周介民(齐峰),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坦然承受沙湾人强加给他的委屈,他甚至不在乎沙湾人包括父母对他的误解。关于委屈和误解,虽然笔墨不多,却显出悲剧的力量和崇高感。以扬卿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使沙湾充满了和谐和诗意,而以齐峰为代表的暴力革命,给沙湾带来巨大的动荡。人们本能地选择和谐和诗意,但最后在当局恶政和制度压迫下,又不得不跟随齐峰上齐天界打天下,成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一员,就连沙湾最大的乡绅佑德公,也从最初革命队伍的幕后支持者变成明确的后勤保障成员。《家山》并非有意展开对改良主义与暴力革命的辨析,在沙湾人的生存法则中,社会发展模式自然形成这样一个发展史和内在逻辑。
陈扬卿是在大地方读书做事的人,背着手走路,不怎么理人。他的新式打扮刷新了沙湾人对衣着的认知:“沙湾数不出几个五黄六月天穿鞋的男人,扬卿却是一年四季都穿鞋的。男女老少只要看见扬卿,都忍不住会朝他脚底下打望。他是穿皮鞋的,沙湾人没有见过。”他要求沙湾人喊他陈老师,沙湾人怕丑,喊不出口。这位“坐在天井里闪闪发光”的人,却在不久之后“打了背包,带十日粮米,腰挎五双草鞋,头戴竹斗笠,手里提剑,溯万溪江南上”准备修建红花溪水库。刚回村时,读者会误以为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一腔救国心,让本县新增上则田一万二三千亩。历任县长支持水利建设,全县开征水利附捐。地下党员史瑞萍留在沙湾教书,两人产生感情结为夫妻,育有四个儿女。
工业化对沙湾的影响甚微,贞一写信说她寒假跟同学一起去裕湘纱厂勤工俭学,不回家过年了。沙湾人对工业化的想象无非是“棉花条子不要人搓,梭子自己长脚两头跑”。长沙早都用电了,再穷也用洋油灯盏。沙湾人坚持点桐油灯,说是祖宗闻不得煤油味。扬卿在这样的零工业基础上修建水库,其难度可想而知。小说将水库这条工程与革命爆发随着赋税矛盾同时推进。扬卿的水库修建成功与齐峰的革命成功证明了新理念战胜了旧传统。扬卿与史瑞萍办新学很顺利。私塾很快被新学打败,李先生讲《三字经》《增广贤文》,“先是有五十几个人读夜校,不到两个月就只剩几个人了”。
有喜是扬卿的工程助手,这位有着理工头脑的地主家的长工,对工程技术一看就懂,一点就通。“天气热得猪打栏,有喜下半日就把三个天井的阳沟半塞了,天井泡凉了才把水放干”。老屋结构有天井,这是一种降温的好办法。陈有喜平常就痴迷日常生活中的工事。有喜是孤儿,八岁给佑德公家放马,悟性好。梆老倌评价他:“有喜知事,又晓得尊卑上下,见人春风儿好,沙湾人哪个不喜欢?”有喜忙说我哪里知事,都是福公公扯起耳朵教的。有喜从小没机会上学,全靠自学,上茅厕都带《三侠五义》。梆老倌敲梆用词不当,他背地里说应该怎样改。他知道“关好门窗,警醒强梁”这样的词句。他入赘竹园村瓜儿家(瓜儿是福太太侄孙女),竹园条件差,种的望水田,有顺口溜委婉地形容竹园村的窘迫:“沙湾死人打丧,竹园叫花子讨汤”,有喜在扬卿的支持下,带领竹园村人建水库,彻底解决了长期缺水的问题。大儿子随瓜儿家姓刘,二儿子跟自己姓陈。
理性是通过教化把自己原始精神异化为一种自我意识。如果说扬卿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对沙湾人的改变是在传统框架之下的旧瓶装新酒:学习新知识总归是有用的,尽管不能考科举。它与人类自我升华的诉求是一个自觉统一体。因此,沙湾人对扬卿的改革是称赞的。齐峰代表的新观念和新制度(蓝图)与伦理实体具有对立的性质,它不具有扬卿的知识理性的直接性,沙湾人一开始对此表现为出排斥和对抗。齐峰的人文主义终极理想——作为理性的最高要求,需要双重否定才能实现,即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否定和对现实精神世界的否定,在此基础上把自己的欲望从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齐峰的父亲修根是狂热的土地爱好者,每攒一分钱都是为了购买土地,土地是他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他对物的热爱的原始欲望不加修饰地表现出来,这个人物是中国农民典型的写照。中国乡土小说的经典大都写了农民与土地的深厚联系。《白鹿原》里的白嘉轩、鹿子霖,《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菊咬筋。西方文学也有狂热地热爱土地的典型人物,如《乱世佳人》(或译为《飘》)中的斯佳丽的父亲杰拉尔德。修根同他们一样,把土地从生产资料上升为精神信仰,他勤劳本分,“屙尿都怕耽搁工的”。齐峰解构了父亲建立起来的精神性图腾,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要让所有庄稼人都有土地。
齐峰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人物,同时也是沙湾人理性升华的一个象征。齐峰年少负笈长沙求学,起初“修根本是不肯放他去的,说读洋学堂又考不得状元,读它有卵用!”修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扬高要他加入国民党,他就加了。他虽然无法理解儿子的事业,但知道儿子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出于父亲的本能,不惜背负公公与儿媳乱伦的污名,设法保护躲藏在阁楼上的儿子。红军过沙湾,救红属,抗战胜利捐谷,他都积极配合。史瑞萍扮演齐峰的同学给修根家送银元,当晚修根家遭抢。实际上是齐峰为红军筹措经费,派人到自己家里“抢”了一部分银元。小说通过这一对父子关系,从对立到融合,表明了精神成长的复杂性、艰难性。这段历史也就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沙湾人对红军的好感是通过细节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细节是,红军过沙湾纪律严明,讲规矩,与之相反的是县政府调查组的强横和贪婪。第二个细节是抗战胜利后,躲凉水界的五十多名红属成为受保护的抗属。陕甘宁边区给他们发的优待证,而国民党抗属却没有,反映了两个政党深入群众能力的差异性。沙湾人理性和觉醒是在对比中产生的,也才有后面抗税暴动,齐峰一呼百应。
齐峰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他曾委婉地劝过父亲修根,要他宽手放账、紧手置田,田置多了不是好事。却遭到修根的喝斥。他又问妻子禾青造反都是错的吗,禾青说真是奇怪了,造反还有不错的?你不要吓我,你屋三媒六聘讲了我,我嫁过来是要和你过日子的。禾青与齐峰结婚后好几年没有生育的迹象。家里人着急要给齐峰安排娶妾,“齐峰一听急了,说:‘妈妈,都民国了,娶什么小?’”齐峰的母亲满莲只好到黑水公公那里给禾青讨水喝。那几日齐峰全县四处奔走,救了上万条人命!齐峰在沙湾没有同道,跟组织联系简单,没有可说心里话的人。扬卿也是开明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同路人,又比他大两个辈份,从小就玩不到一起去。与劭夫(陈齐美)玩得好,劭夫不在家。修根和满莲都是勤俭持家的地主。做针线就要坐到门槛上。一家人的衣裤没有几件不是补过的。修根有一天问:“齐峰,你洋书读了这么多年,如今也在洋学堂做先生了。你告诉老子,到底学了些什么?你不信佛不信道,到底信什么?”齐峰忍了半日,才说:“我信的,不在皇土之上。”修根以为他信了洋教。这一段对话点到为止,用意深刻。齐峰是孤独的,他的事业需要超强的内心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二、诗意掩盖的清晰逻辑和因果关系
小说诗意的语言洪流缓慢地流淌,矛盾隐藏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处处都是美丽的乡村画卷、美好的人情关系。沙湾人的饮食起居,山川美景。沙湾人自己身处美景而不自知,以至于他们也是美景中美的要素。小说开头就有一个美学基调,作家给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桃香设置了一个冬日暖阳的场景,桃香坐在暖烘烘的太阳底下晒糍粑皮,炒米,纳鞋底,用响竹竿赶麻雀,屋角下一排排簸箕,一群麻雀在簸箕和柚子树之间起起落落。作家将这幅充满暖意的情景向更远处延伸。以桃香家的地理位置给沙湾村画了一幅全景图。“从柚子树下望过去”(表明桃香家在半山坡上)。一幅风景画尽收眼底:西边的豹子岭,东边齐天界,中间宽阔的田野,万溪江,远处的山没入云天,山上有虎、狼、熊等野物。所有沙湾村人都是这幅全景图的具体细节。作家将每一个细节撑开,使这幅全景图饱满有力。沙湾不是世外桃源,人们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所有的悲欢与生死都与外面的大世界紧密相连。现代报刊、电报的信息化变革,祠堂改作学校,其作为信息中心的功能被取代。扬卿与史瑞萍的情书,充分发挥《诗经》的赋比兴功能,古雅高贵,情感节制,乐而不淫,自由恋爱的灵魂与远古的浪漫主义完美对接。但乡村学校授课方式、课堂情景,尤其是音乐课又是西方模式。洋为中用,并无违和感。逸公老儿以及沙湾读书人聊天以天下家国大事为中心。精英层与普通民众并没有形成壁垒,倒有一种“渔樵耕读”的理想汇合。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沙湾村这样的富裕村整体呈现着“渔樵耕读”的古典浪漫主义氛围。沙湾毗邻县城,四季农活儿夹杂着产业经营的细节,手工作坊、以及小买卖的工商业气息。农耕文明的乡村精英对代表先进文化的工业文明毕竟有抗拒心理,接受起来总是慢半拍。这种慢导致沙湾人必须面对不期而至的现代化难题。20世纪上半叶,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沙湾村平静祥和的古典浪漫主义节奏。为了与时代同步,沙湾人最后做出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的举动。
作家笔下的沙湾人民表面过着祥和安逸的生活,实则动荡不安,时时刻刻激流暗涌。富足的沙湾也经不起折腾,最后民怨沸腾,发生暴动。他们在二十年的光景里,在小小村庄经历了农会、宗族、恶势力多方力量较量,经历了赋税制度花样翻新,军政交恶,政治乱象丛生,匪患不断,官绅矛盾突出,男女平权冲突,杀红属,抗战抽丁征兵,参加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历史巨浪。沙湾人经历的每一桩事件,都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侧影。但《家山》并不显得是一部革命斗争史,作家将这些“好看”的要素按压下去,按照沙湾人日常生活自然流淌,用诗化的语言从容铺排,所有的事件也随时间顺序自然一一呈现出来。表面看起来多肉少骨、结构模糊,被放大的冗长的细节显得散淡、悠闲,甚至不惜篇幅地展开扬卿与史瑞萍的恋爱过程。但正是这种慢功夫见出作家的叙事功力,也正是这种平淡无奇显现作家塑造人物的能力。
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王跃文在小说写作方面的开拓创新的雄心,他大胆抛开长篇小说必须遵循的艺术手法,如情节的悬念和冲突,结构上的复杂多变,意象的设定,多重隐喻暗示等。他一反常规,大道至简,在看似混沌的情节中,从人物的言行、状貌中展现清晰的底层逻辑和因果关系。他也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将动荡和不安隐藏在宁静悠远的审美要素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小说也一样,无所谓结构和机巧,万事万物自然展开,生生不息。过于运用技巧,反而影响表达的力量,不如顺其自然。小说的氛围营造延续了他的中篇小说《漫水》的写法,人物性情淡泊,气氛冲和、灵魂虚静、气质空灵。个人的悲欢也显得从容大气,人的灵魂也变得深刻厚重。作家想要写一部好看而有力量的小说,尝试用纯粹语言模式挑战繁复的技巧。情节的迭宕起伏,结构的眼花缭乱在康德看来是一种低级的美,因为它带有病理学上的刺激。康德认为这种刺激是“外来分子”,愉悦是一种纯粹的美,“因为没有任何利害、既没有感官的利害也没有理性的利害来对赞许加以强迫”。《家山》正是追求这种无病理刺激的纯粹的美。
这种静水流深的结构对人物塑造同样也是一种挑战,人物都不具备传奇经历,即使像扬卿、齐峰、劭夫这样本质上具有传奇经历的人物,作家也有意让他们“低调”,并不刻意突出他们戏剧化的人生。沙湾人都在日常琐事中不露痕迹地生活着,他们个人没有机会经受重大而艰难的事件考验,大事来临都是集体面对,集体解决。如何塑造这些数量众多的平凡而普通的人物,这是对作家写作能力的考验。沙湾龙头杠一样的权威人物是佑德公(陈修福),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生死大事,但这位沙湾村举足轻重的人物,形象丰富饱满,甚至颠覆了过去文艺作品中乡绅地主的刻板印象。他的外形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标准打扮,穿着黑缎面起团花的长棉絮袍,头上戴的皮帽子,手里铜烟杆光亮光亮。“佑德公家的大窨子屋同陈家祠堂隔着一片松林,松林间春夏都会落满白鹭。”一派大户人家的场面。有军官儿子劭夫(陈齐美),女儿淑贞、贤贞、贞一。佑德公家有三百亩良田,还与历届县长私交甚深。他没有像大多数文艺作品中的地主那样作恶多端,而是一生行善积德。当然,佑德公仍然是一位守旧的乡绅,在做道德框架之内他认为好的事情,凭着尊重生命、家国兴旺的本能帮助乡邻、救红属,捐谷劳军,支持暴动。他的知识结构没有达到追求平等自由的境界,因此,他为了延续后代给劭夫纳云枝为妾,以最大的善意把凉水界800亩山林和80亩良田赠给了亲家作为彩礼(亲家坚辞不受)。他给家里的长工有喜安排入赘竹园刘家。他支持新思想新事物,使得沙湾村成为当地先进文化的代表。另一个人物陈远逸(逸公)出场不多,他是癸卯科举人、前清知县。三个儿子都在东洋读过书。大儿子扬甫在上海做医生,老二扬屹在国民政府当差,满儿扬卿日本留学后回家侍候爷娘。把一半房子赠送给叔伯兄弟陈远达一家。送的过程吃亏不讨好,达公一家人多地少,租种佑德公家的土地,达公老儿养了六个儿子,老六扬高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经历了沙湾所有大事件,他凭本能做事,在德性和理性上的修为尚浅,不自觉地扮演了阻止文明前进的角色。对于这两家的评判,作者有勇气呈现了一个富人道德高尚。穷人穷凶贪恶的二元结构。反映在中间人物的塑造上,陈齐树、朱达望、四跛子等,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优点和缺点。陈齐树是沙湾村的知根老爷,家藏远近几个村的鱼鳞册,官厅收地丁银都得经他家的手。他家不像佑德公和逸公老儿祖上有过功名,但每代都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人,也被官厅和乡邻们看作绅士人家。这样一位尽职尽责的知根老爷落得被恶人打死的结局,可见当时的土地赋税矛盾的尖锐程度。朱达望祖上是沙湾原住民。很早以前,沙湾是朱家的村子。姓陈后生娶了朱家女儿,这后生就是沙湾陈家的祖公老儿明勋公。陈家人越来越多,朱家人越来越少。陈齐岳(梆老倌)负责沙湾敲梆打更的工作,儿子有续、有统成为齐峰组建革命队伍的好帮手。
《家山》在人物塑造上开启集体平民英雄的模式。像修岳、有续、有统一干沙湾青年为齐峰的队伍做出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在五十四万字的《家山》里,他们属于极不起眼的一群人。五疤子(有仙)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具有成长性的人物,用剃头匠马师傅的话说,“听他讲话梆硬的,鸡都啄不烂,长大了只怕不是个善伢儿”。五疤子早出晚归,到江东场坪上赶场偷东西,被人绑起来吊在槐树上打。沙湾人看不过,给他壮气。五疤子回沙湾后并不悔改,说我自己做事自己当,关哪个卵事。齐树给他整家法,装在家法笼子里,让人轮着上去打屁股。沙湾抽丁时,五疤子替人顶名额,竟然发展成一门生意。经劭夫的教化,成为抗日英雄。五疤子被整家法,是《家山》中为数不多的宗族利用私刑教化族人的案例。传统家法族规对维护治安、国家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统治者使之“成为封建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沙湾人心理上普遍认可对五疤子的教化。农村天高皇帝远,也正是这套家法规约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成长为符合道德标准的人。宗族社会在关键时候有凝聚力,抗战胜利,沙湾村五百人担谷劳军。第二年遭遇洪灾,田地颗粒无收,到邻村借钱借粮挺过饥荒。沙湾村在这两场事件中集体表现出团结向上的精神。修碧是机枪手,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乞讨回乡,小说关于修碧刻画不多,但包含了多重含义。朱克文是沙湾朱家的长子,他的优秀品质不输任何陈家子弟,他作为县警察局长却暗中救了齐峰。修根误以为是克文害死了齐峰,见到克文就要拼命,克文忍辱负重。沙湾青年读书人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踊跃参军。在大事件面前沙湾人为家国着想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个骑马坐轿都有规矩的小村庄,显出较高的整体道德水准。这一写照正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整体状态,小说在民族精神塑造方面因此具有典型意义。
三、围绕赋税核心问题的人物群像
小说在官吏的刻画上用笔吝啬,沙湾所在的县走马灯似的换县长,这其中李明达是被着力书写的一位。小说反映的年代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从建立到灭亡的时段,这二十多年始终没有形成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中心观念漂移,地方主义抬头,形成了若干相对独立的板块和结构性裂缝。”地方保持较强的独立性,与中央的关系貌合神离。县政权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各种复杂的关系。县长频繁更换。李明达被联名举报,去职前与扬卿辞行。“扬卿望着李明达,说:‘我也隐隐听到些风声,你得罪了一些豪强大户。你那个布告不给那些自以为有面子的人以面子,我读的时候很解气。’”李明达也借此机会一吐心中块垒。李明达的新政就是改革赋税制度。自民国以来沙湾村深陷以土地为核心赋税纠缠之中。李县长谨遵总理遗训,民国以来,党国遵守总理遗教,晓法喻理,倡导革命精神,而致民心向上,乐输国税蔚然成风。他是个建党治县都很勤勉的人。他立志发展国民党员,要“消除国民党员空白村”,他借佑德公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将新政意图转换成民意:《激流报》头版粗字标题:《佑德公倡议赋从租出,全县民众齐声赞同》。扬高看后很气愤,他把报纸给了修根,说听了半日的会,原来是佑德公的名堂。事实证明是这一个矛盾重重的政策。扬高站在佃户的立场上反对田赋都由佃户出,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对立起来。
陈扬高是《家山》中复杂多面的人物,这个人物塑造难度较大。他一方面自私、狡猾、傲慢,二十几岁是就是沙湾农会执行委员,腔调很高。充分利用手中权力打击异己,反对克文在村校任教,只因克文不是陈姓家族的人。抗战抽丁抓阄抓到陈姓子弟,他就扯心扯肺地痛。他的利益关联由内而外,在沙湾村与外界发生利益冲突时,他眼里只有沙湾村,宗族利益又成为次要矛盾。他自己是佃农,他代表佃家立场。扬高说:“我佃家一年到头又是人力,又是牛力,又是肥力,起早贪黑,还要分担附加?田业人家坐在家里也只分担一半附加?”向远丰反驳他说:“你的工作是协助乐输。田业人家出了田地,收益是正当的。”有人评价扬高的儿子修岳脱种了,与父亲品性相反,为人正直善良。扬高同时又有善良仗义的一面,他在保护红属方面也出了力,佑德公说:“保住这十一户人家,高坨是尽了大力的。乡公所和县政府要他查红属,他瞒得天紧。”他虽然不理解齐峰的行为却没有揭发他。但也不认同他,“扬高也来了,进屋就高声大气,说:‘我早心上有数,齐峰是共产党。今日才晓得,他就是周介民!他做什么不行,硬要做共产党!害了一屋人!’”他的一番言论被扬卿喝住。扬高身上的品质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人自在利益攸关时的本能选择,他的未经提炼的理性无论在传统文化里还是新知识里都与他的位置不相称。
向远丰作为县里的乐输委员,同知根老爷齐树一样对复杂的赋税有自己的理解。沙湾各种身份的人,地主、自耕农、佃农、长工、短工,他们的赋税捐徭各有不同。向远丰要沙湾成为赋从租出的模范村,交满十成。齐树坚决认为只能交七八成。认为盘古开天地就这样,总有天灾人祸,总有三病两痛,完不成赋税的人家总是有的。沙湾遭灾,到凉水界、竹园、舒家坪借谷,遭洪灾的地方免租不成,各种地方附加比田赋反而多四倍多,还额外多出桥梁捐、义渡捐、茶亭捐。知根老爷齐树被人谋害,连世代良民佑德公都要做抗欠大户,普通老百姓更负担不起。扬高和全保十三个甲长在粮库被关黑屋。修岳带人烧粮库,乡公所的人朝老百姓开枪,有龙出于自卫打死了人。扬卿责备扬高说:“你当保长的不晓得息事,不晓得讲理,你要害死沙湾人!”扬高眼睛血红说:“你是读书读蠢了!如今哪是讲理的时候?你去讲你的理,我去打我的锣!”扬高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这也是齐峰潜入沙湾组织武装暴动成功的基础。
四、桃香的焦虑及沙湾的女性生存图式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娜拉走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感叹如果经济制度改革了,上面的话题就不必讨论,“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他写《伤逝》,子君回乡以后也只有死路一条。近几年又有长篇小说着力塑造民国时期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胡学文的《有生》中的那位一百多岁“半死之人”祖奶;陈继明的《平安批》里集智慧与威严于一身的九十多岁的阿嬷(老祖)。她们都是民国女性的极端个例,她们的特殊性取决于自身天才与后天的锻炼,与知识无关,她们都没有机会进学校。
《家山》中的女性塑造是有层次的,追求人类整体的自由是第一个层次,史瑞萍是一个代表性符号,他是知识理性与制度理性的中介。第二个层次是推己及人追求个人自由,贞一是这方面的代表。她有信念支持,达到理性自觉的层面。第三个层次是反抗强加给自己身上的不合理的东西,银翠和月桂做了艰难的斗争。第四层是传统不合理规定的践行者和守卫者,她们是桃香、福太婆、云枝和容秀。瓜儿、禾青等众多沙湾女性是随大流的,不具有革新或守旧的意识。大多数人没有能力觉察到社会结构的深层原因,甚至看不到资源分配不公的表象。她们的信条是“认命”或“从来如此”。《家山》写出了当时女性真实的状态。贞一鼓动放足,结果还落得一身不是,史瑞萍出面以旧习俗挽救了银翠的生命和婚姻。
桃香嫁到沙湾村后,大家对她的印象是打虎匠的女儿胆子大,讲话抓理,高矮都不怕,她拥有“出口成章,四六八句,沙湾没有哪个讲得过”的辩才。她打赢了官司,享有进祠堂坐上席的权力。被尊称为“乡约老爷”。她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对童养媳来芳的压迫,强迫女儿月桂裹足。桃香践行“女儿,还是包个小脚好看些”。这个想法与人物的身份相称,她的美学行为受周围人的支配,她没有独立自我意识,无法识别社会和经济利益强加给她的审美陷阱。“包你个尖尖脚,看你往哪里跑!”吓唬孩子的一句话反倒说出了包小脚的真相:限制行动自由,她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她同时又要求儿子“落得地,就开始学打”。男人就应该赋予他力量和自由。桃香同时也是思维严谨的人,她去县里打官司,髻子梳得紧实,头发油亮亮。她自己的一双大脚随时遭到嘲笑,轿夫抬她说“吃半升米抬人,吃一升米抬脚”。扬卿希望齐明继续上学,桃香与四跛子对知识的定义也仅停留在识字的层面,不再供十六岁齐明读书,逼他跟大他四岁的来芳圆房。
贞一和月桂是两种不同的反抗方式。贞一是佑德公的女儿,有机会看到看了《湘报》《大公报》《湖南公报》上的新事物,她开始怀疑人生,说,“哥,我就是那只蟢子,只能守在自己的网子里,到老到死。”她朦朦胧胧地感受到外面的变化,在长沙周南女校接受新知识后,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身边的女性,给县长写关于妇女放足的呈情。贞一力推废除裹脚习俗。给县长的呈文得到回应后,在乡里推行禁止裹足。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在月桂放脚事件上,桃香顽固的守旧观念导致女儿月桂的脚半残。县长亲自给妇女放足,以示禁止裹足的决心,月桂也是被县长亲自放足的重要典型。女儿家的脚被陌生男人摸过被视为玩亵,贞一被桃香指责。沙湾女性反传统反体制的唯一出路是尼姑庵。月桂反抗裹足的最后打算也是“落庵堂”,对于乡下女子,这是很真实的情景和出路。月桂最后出家当尼姑,她的反抗充满了悲情的力量。
关于妇女解放,农会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则为着平等自由,二则为着农民教育。人分男女,财有贫富,都应平等。民国时期也做过不涉及土地制度的改良农业的尝试。佑德公说:“沙湾农会只办了两件事,就是准许妇女进祠堂烧香拜祖宗,还说不准女子包尖尖脚。”劭夫提醒爹,禁止女子缠足,清朝皇帝就有谕旨,只是老百姓自己不听。民国时期已经有自由恋爱的风气。扬卿与史瑞萍的自由恋爱用大篇幅渲染,而银翠与修岳的恋爱,却是有伤风化的大事。银翠娘要她在一根绳子和一把刀中做出“选择”,银翠第一次享有选择的权利,这是莫大的讽刺。银翠的哥哥朱克文从中周旋,补齐程序,请史瑞萍做媒人。
没有社会制度和男性的支持,女性无法取得独立。贞一的母亲福太婆是思想守旧的代表人物,极力阻止贞一上学。银翠娘、容秀、云枝则是不自觉的旧思想的捍卫者。家谱、祠堂不仅压迫着女性,同时也是套在男性身上的枷锁。劭夫是一位有理想、道德品质优秀的青年,他是打入国民党内部当上师长的共产党员,与齐峰里应外合发起暴动。但他的思想解放没有齐峰彻底,妻子容秀没有生育,家里给他安排娶妾传宗接代,他欣然接受,得知小妾为他生子,“喜极而泣。劭夫今日有后,虽百死亦不足惧耳”。佑德公认为中山先生遗训跟《礼记》是相通的。他们懂《礼记》的核心思想,同样也懂《礼记》中孝的意义,劭夫的一妻一妾都以延续后代为人生目的。“只要说到生儿育女的事,容秀背上就出汗。”云枝则是因为对劭夫的爱慕,死心踏地地当妾。容秀、云枝身上拥有传统妇女的美德。沙湾祠堂供奉的祖宗牌位,以及每隔一些年份都要修订的家谱,既是沙湾人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精神枷锁。小说写到祠堂神龛上供着两尊祖宗雕像,一位是文官光神,牌位上书“始祖明勋公神位”;一位是武官光神,牌位上书“显祖敬远公神位”,这是沙湾陈家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压力与动力的根源。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