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可礼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有幸成为较早的读者,受教之余,不无怅惘。文集精装六册,墨绿色的封面,装帧大气,低调沉稳,就像张可礼先生的为人为学,温雅平旷,谦和朴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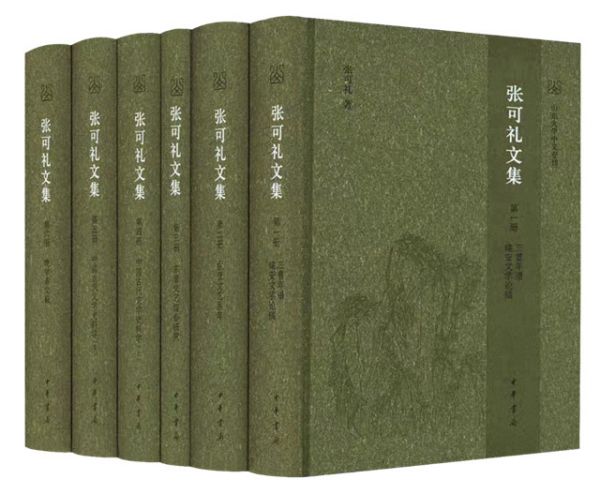
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张可礼先生贡献卓著,人所共知。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能有多少人深知张可礼先生的学术成就,实不好悬测。毕竟隔行如隔山,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则趣闻。刚刚去世的杨义先生,名声不可谓不大,但出了学术圈,就未必如此了。网上流传一篇纪念杨义先生的文章,一条跟帖评论说,杨义的去世是相声界的重要损失。显然,这位看官根本就没有读文章,只看标题,就把文学所的杨义与说相声的杨议混同起来。于是,又有一条跟帖建议,纪念文章最好先介绍一下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和具体贡献。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于是,我想先介绍一下张可礼先生的简历:1935年生,山东荣成人。195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62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山东大学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陆侃如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1990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2021年2月6日去世,享年86岁。
在上述经历中,1962年对张可礼先生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那年,他考取了山东大学著名学者陆侃如先生的研究生。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张可礼先生的人生轨迹,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矢志不渝地研究汉魏六朝文学,这部《张可礼文集》记录了他毕生的主要成就。
当然,他不是唯一的幸运者,还有两位同学和他一起追随陆侃如先生读书,同样取得了重要成绩,一位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刘文忠先生,另一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祖美先生。按年龄排,张可礼先生第一,刘文忠先生第二,陈祖美先生第三。刘文忠先生、陈祖美先生先后在不同单位工作过,张可礼先生的经历则比较简单,研究生毕业就留校任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教学科研岗位。
三位老同学性格特点不同,遭逢际会不同,做事风格也不同。张可礼先生说话总是慢声细语,生怕打扰别人似的,那是一种发自天性的礼貌,让人感到舒适、亲切;刘文忠先生很直率,嗓门高,说话常常直言不讳,这种性格难免会得罪人;陈祖美先生看似温婉,实则为女中豪杰,据说年轻时酒量很大,做事也雷厉风行。
他们三位都好学不厌、著述不辍,走的路径却又不同。张可礼先生走的是长线:生活有规律,每天按时作息,很少“开夜车”,持之以恒。刘文忠先生则不然。他大学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1962年考入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换了好几家单位,最后二十多年落脚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当编辑,需要天天坐班,又要天天看稿。我和曹道衡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就由刘文忠先生担任责编。1998年年底,我从他那里取回校样,里面夹了三百多张纸条,上面写得密密麻麻,都是校订意见,我既惭愧又感动。譬如颜之推的生卒年,《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未详载,《颜氏家训·终制》也只是说“吾已六十余”,但同书同篇又说“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似乎是指太清三年(549)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饿死之事。最初,我们怀疑“十九”为“二十九”之误。因为《周书·颜之仪传》记载,颜之推的弟弟颜之仪卒于开皇十一年(591),年六十九,颜之推年长于颜之仪,“二十九”更为合理。刘文忠先生则不以为然,他指出,《颜氏家训·序致》云“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即指其父颜协之死,据《梁书·颜协传》,颜协卒于梁大同五年(539),与《序致》正合。至其“十九”岁,正是侯景攻陷台城之年。在那三百多张纸条上,类似这样的商榷讨论,所在多有。《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出版后,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作为责编,刘文忠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至今难忘。
刘文忠先生编、研兼顾,只能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为此,他为自己制定了利用“三一”的苛刻计划:每天开夜车,这是一天的三分之一;充分利用星期天,这是一周的七分之一;80至90年代中期,编辑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这是一年的十二分之一。他几乎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过觉,有时还要开夜车至凌晨三四点。就这样日夕披览,孜孜不倦,长年累月,强攻死守,刘文忠先生硬是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勤奋写作,出版了二十多种著作。这是以透支身体为代价的无奈选择。
他们三位承师问道,最初都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后来各有分张。张可礼先生初心不改,始终坚守在这个领域,而且主要集中在建安文学和东晋文学。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精耕细作,细水长流。刘文忠先生就像一颗螺丝钉,在坚守专业领域的同时,不得不围绕着出版社的要求,随时被调用。他做过注释、今译、鉴赏、校点、改编等工作,著述总量不下四百万字。
陈祖美先生从汉魏六朝文学出发,编著《谢灵运年谱汇编》。在我的印象中,她写的《蔡文姬评传》(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最漂亮,最有深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蔡文姬的坎坷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成就,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如文姬归汉的时间、《悲愤诗》的真伪等,资料丰富,考订严密。后来,陈祖美先生转向宋词,对李清照情有独钟,有《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清照新传》(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漱玉词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李清照诗词选》(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著作。陈祖美先生的研究,坚持用女性视角,从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对作家作品作多重阐释,别有会心。传统的观点认为,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就负笈远游,因而李清照的创作颇多哀怨。陈祖美先生则考证出赵明诚并无外出读书、做官的经历,认为女词人的哀怨有着更复杂的内涵。陈祖美先生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不能遽下判断,仅就其所举的例证看,我认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些年来,她每有新著出版,总会送给我学习。可惜我的专业范围比较窄,对宋代文学所知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评价陈祖美先生的成就。1991年夏秋,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十年后,来到文学所工作。不久,文学所评职称,有四十多人申请正高,仅有六个名额,陈祖美先生顺利当选。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研究实力。我最后一次见到陈祖美先生是在2018年8月30日,那时,她已患病住在重症监护室,我去医院看望,只能隔着窗户默默祝愿她老人家早日康复。
三位前辈学者,笃学修行,不坠门风。他们的研究成果,“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背后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动力,更有一种叫人敬佩的忘我境界。
三位先生中,我和刘文忠先生认识最先,和陈祖美先生相处最熟,与张可礼先生虽是最晚相识,但由于专业相近,了解却相对较多。
1995年11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程千帆、周勋初先生代表主办方出席会议,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学者,如罗宗强、袁行霈、张可礼、钟优民、穆克宏、张少康、俞绍初等先生也参加了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可礼先生,他面容清癯,声音柔和,说话时身子总是微微前倾,十分谦和,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会后,我把会议期间拍摄的几张照片寄给张可礼先生,他回信说:
跃进先生:
近好!这次在南京大学有缘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您治学,沉潜往复,不尚空论,且不断有大作问世,极为敬佩。最近几年,我想围绕东晋文艺,作一点综合探讨,在这方面,请曹先生和您多加指导。
我在南京会上提交的拙作,回来后,个别地方又做了修改。今呈上,请审改。如有可能,请推荐给《文学遗产》,予以发表。若不符合要求,或有困难,劳您退回。此事,请千万不要为难。
购买《文选》六臣注一事,我已让我带的韩国硕士生吕寅喆请他父亲代买,只要韩国尚有此书,买到当无问题。
请代问曹先生、公持先生好!即颂
阖府纳吉
附:身份证明、论文。
张可礼
1995.11.29
不久,张可礼先生如约将两大厚册奎章阁本《文选》寄给我。这本书对我从事《文选》《玉台新咏》的研究,帮助极大。我向他表示感谢,他鼓励我说:
跃进君:
惠寄的大作、手书并书款,均收到,请释念。春节后购得《中国古籍研究》上面刊有高著《玉台新咏版本研究》,当即让研究生阅读参考。君风华正茂,且不断有论著问世,可敬可喜!衷心祝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恭颂
撰安
张可礼
1997.4.29
1997年年底,我们一起到韩国顺天乡大学访问,同宿一室,对床夜话。第二年,我们又一起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参加六朝文学研讨会。那次大陆有23人赴会,有关部门指定我和张可礼先生作为联络人。开会那天,张可礼先生进入会场,马上意识到主席台后方的布置有所不妥,便与会议主办方协商。在张可礼先生的要求下,问题得到解决,会议顺利召开。从这件事看,张可礼先生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
与张可礼先生接触越多,对他的为人处世、读书治学的特色认识越深。如果用关键词来概括,我想到了平和、笃实这两个词。
平和,是张可礼先生的最大特色,处世平和,为人平和,治学平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贫农家的孩子,能在大学当老师,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因此,他对生活始终抱有一种感激之情,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他的亲友,感谢他的老师,感谢他的学生。他的这种感念是真诚的,达到一种念兹在兹的程度。
张可礼先生大学毕业留校,行政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还遭遇到很多不足与外人道的委屈和挫折。所有这一切,他都能坦然面对,并尽可能地化解开来,从中体会到某种人生的理趣和情趣;甚至,他还会把这种理解之同情投射到古人身上,心有戚戚,触事感悟。《荀子》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张可礼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说自己比较笨拙,没有才气,能为大家做点事,心甘情愿,绝少抱怨。同时,他还坚信勤能补拙,不论多么繁忙,做完行政工作,只要有机会,马上伏案读书,静心思考,拿得起,放得下。他读书治学,举要提纲,不温不火、不骄不躁,从无懈怠,几十年如一日。他说自己“能在学术探讨上取得一点成绩,是长期勤奋耕耘的酬报”。这种忘我的投入,既是爱好,更是一种事业心。他在《我的求学与学术探讨之路》一文中说:“对于古代文学的探讨,不能拘于职业,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事业,要有事业心。”“有事业心者,源自责任,会超越自我,思想境界会更高一些,会有持久的耐力,没有休息站,只有加油站,不断地向前进,能摆脱‘俗谛之桎梏’,突破多方面的限制。”一段平常话,一生事业心。
由此看来,平和不是平庸,不是平凡,而是有感激,有原则,有坚守,符合古人所推崇的中庸之道。
张可礼先生的研究看似平和,却很笃实,多有独创。他每研究一个课题,总是从资料编纂做起。研究建安文学,先有《三曹年谱》;研究东晋文艺,先有《东晋文艺系年》;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业绩,先有《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建立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之上,又能注重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张可礼先生的研究往往能援据精博,掇其大旨,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譬如,东晋文艺研究就是张可礼先生辛勤耕耘出来的一方学术沃土。《东晋文艺系年》把东晋(包括北方十六国)一百零三年的有关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方面的史料,以时间为序,分别系于各年,涉及一百七十多位文艺家,详略去取,各有裁制。以此为基础,他撰写的《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一书,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极大地拓宽了中古文学研究的天地。
1999年12月28日,张可礼先生给我写信:
跃进先生:
去年此时在台湾见面后,一直没有联系。从一些学术刊物上,知道您不断有大作问世,非常敬佩。年来,我主要时间用于带研究生,潜心读书时间较少,长进甚微。最近两年,我在教学时,再次阅读了陶渊明的诗文,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对陶做一点新的思考,结果是草就了一篇拙作《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拙稿已挂号寄给了《文学遗产》编辑部。您文献根柢深厚,有理论素养,思维又活跃,请不吝斧正。如符合要求,希望能予刊用。如不合要求,就作罢。请千万不必为难。元旦吉日在即,恭颂
阖家幸福
张可礼
1999.12.28
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上。“三要义”指陶渊明诗文中蕴含的三重独特的涵义:第一个要义是指陶渊明努力保持自己的自然之性。他的挂冠归隐“与其说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倒不如说是为了追求自由更为准确些”,这就在客观上反驳了一种成说,认为陶渊明辞官归田是一种有意的政治行为;第二个要义是指与诗人倡导自然之性相联系的“热爱自然之景”和“遵从自然之理”的特性。陶渊明有生存的压力,有文化的压力,更有死亡的压力,但他成功地借助于自然之理纾解了这种压力,超脱而不厌世,宁静而不消沉;第三个要义是指追求和谐的境界,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陶渊明曾经历过官场生活,看到了官场的虚伪和欺诈,这是他追求和谐的生活根基。这篇文章,作者使用的材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推论好像也不新奇,但其文字隽永悠长,其结论别有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
张可礼先生看似平静如水,但内心极重友情。《晚学斋文薮》专辟“为师友作”一类,收录了张可礼先生情之所寄的十余篇回忆师友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曹道衡先生在文学史料上的重要建树》一篇。2006年,张可礼先生不顾高龄,不避炎热,亲赴芜湖参加“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作长篇发言。当时的他语调低缓,感思兼伤,大有“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的惆怅悲凉。那天,我就在现场聆听,切身感受到张可礼先生的那份山阳闻笛的深情。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先生告诉我,张可礼先生去世时,正值疫情肆虐之际,家人遵照张可礼先生遗愿,没有通知文学院,丧事既毕,始通知亲友。不仅如此,张可礼先生生前还挑选若干自己心爱的藏书分赠友朋。张可礼先生去世两个月以后,其哲嗣遵照遗嘱,将六种藏书赠给杜泽逊。在《张可礼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泽逊先生持书到现场,将批语展示给与会者,以表怀念之情。聚散固人理之常,然念师遽逝,泽逊先生展书情塞,致叹良深,那情景让人动容。
《张可礼文集》收录《三曹年谱》《建安文学论稿》《东晋文艺系年》《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晚学斋文薮》六种著作,共330万字。在同时代学者中,张可礼先生不算高产。从张可礼先生的自述中知道,他还有三部著作没有收录到《文集》中,一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二是《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三是《二十世纪世说新语——趣闻逸事》,从内容看,分量应当是很大的,也很有趣,很重要。无论如何,将来有机会都应当收录到文集中,这是我所特别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