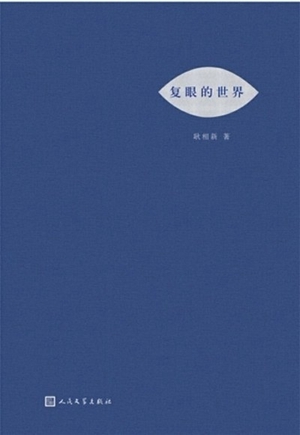
《复眼的世界》,耿相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当代诗坛上,耿相新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都是陌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诗作会带着某种独特的美学纹路和别样的精神气息,会有其他诗人无法替代的特定意义和独到的艺术感染力。了解耿相新的吴思敬老师称这位诗人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勉学之士,学贯中西,博今通古”,我想这一定是知人之论,绝非简单的溢美之词。在耿相新新近出版的诗集《复眼的世界》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作为饱学之士的诗人渊博的知识储蓄和对大千世界的深切领悟,尤其是诗人以科学的眼光来烛照世界,将科学的认知默默渗透于字里行间,从而达成了科学与诗的联姻,在我看来这正是耿相新诗歌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了我们窥探诗人的情感指向和思想踪迹的重要路径。
科学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境遇和心灵感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变更和持续刷新着。而今,科学已然浸漫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理解和懂得科技知识,成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懂得生活与世界的最重要方式。在耿相新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篇章鲜明袒露出以科技理解生活的旨趣,尤其那些对科技术语加以艺术诠释的诗章。《秩序·量子态》写道:“梦里,我练习如何去爱/数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之外/另一个我,也在练习/这不是奇迹,我是一对粒子/因为你的光临,叠加态的我/塌缩成一心一意,爱/这个世界,由此而形成”,诗人拟想了一种爱情的情景,将“量子态”这种“微观粒子所可能具有的状态——能量状态”加以形象演绎,显得别有意味。再如《暗物质》:“你不能否定,你是透明体/每一毫秒/无数物质,粒子正穿透你/它不是光,它是隐身的高手/它不惊扰任何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粒子,它只是无意识地,想穿透你”,搜索“百度”可知,“暗物质是指理论上提出的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它可能是宇宙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又不属于构成可见天体的任何一种已知的物质。”诗人以个体每时每刻都被“暗物质”穿透的形象描述,来强调“暗物质”的无处不在,达到了以诗歌来形象讲述科学的表达目标。
在被高科技所覆盖的现代社会,人类的心灵空间和精神现象,无一不是科技牵动下所生成的结果,因此,对人类心灵世界与精神活动的确切诠释,往往需要借助科技的援助才能真正实现。耿相新的很多诗歌,正是以科技为基本的思想武器,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形态和精神状况的生动阐明。诗人以“算法”来解释人类意识:“意识,也是一种‘算法’/在人的神经网络里/意志自由,神圣的读秒时间/也成为了,可怕的既定”(《“算法”》),用一种确定的数学方式要阐释不确定的人类意识活动,这是不乏新意的。对于人与人之间可能天然存在着某种屏障与隔阂,诗人从“宇宙墙”的宏观视点上加以烛照:“那堵不存在的墙,隔开了谁?/谁,以一个复数的身份,参与了墙/的证明,每一个谁,都是一个/平行的平等的宇宙,像时空中的千岛/因为墙的存在,我们需要隔墙,对话”(《宇宙墙》),诗人将每个生命个体都比作一个“宇宙”,然后进行合理的推理与演绎,既然外在宇宙都有墙存在,那么人与人之间必定也隔着一堵墙,这样,人与人之间要想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就必须“隔墙,对话”,这样的诗意言说,显得情思涌荡,妙义横生。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我的审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不仅认识方式变得丰富多样了,而且审视路径也显得更为细致和深入,由此,人类的情感反馈和思维特征也相应地出现了诸多新的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发展对人类的改变,最根本的是对人类情感世界和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显著改变。基于对科技知识的了解和熟悉,耿相新还从科技创生的新世界中,领悟到不少富有睿智和哲思的生命真髓,并用分行的文字加以艺术的表述。吴思敬老师评价说,《复眼的世界》是“一部文人之诗,一部哲人的思想录,一位精神漂泊者的歌吟”,诚哉斯言!在《复眼的世界》里,那种经由科学智慧而领悟到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卓见与真知可谓俯拾即是。《秩序·原子》强调了原子是构成事物的最基本物质单位,原子组合让物质有着本然的秩序,而“测不准”又是其中不可违逆的物理定律,宇宙间这种格外吊诡的情势之存在,极大凸显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诗人这样写道: “但更多的,是最不可思议/测不准,它们没有方向,完全不知道自己/它们由一瞬间一瞬间的迷茫组成/意识指挥不了行动,它们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它们企图在有限的空间,战争/逃逸,寻找自己的轨道,位置/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它们的命运是无序/正是这些无序构成了有序的原子/理性的根深扎于非理性,这就是/物质世界,一个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世界”。可想而知,“测不准”这一科学观念,对诗人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物质世界,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以“测不准”观念为着眼点,诗人对现实世界和人类命运生发出深沉的反思,从而书写出充满哲思的诗行。在耿相新的诗集中,这种充满哲思的诗句随处可见,如“‘生活在别处’,我们已深陷于/一根线,它是一堆0和1的数字/它将代替你,它将计算你/你唯一挣扎的,只剩下,闪烁的意识”(《生活在别处》),“黑暗是如此美丽/一支短短的蜡烛就能将它点燃”(《受了伤的眼睛》),“我,诞生于空无/我,向着空无,超越”(《本我》),“长得也许是一种悲剧/可是,停留于儿时更是一种,侏儒”(《儿时的记忆》),“受伤的不是口感,而是眼神”(《光在哪里》),“我们洗去了面具上的灰尘/却没有治愈脸上的伤口”(《分裂》),等等。而这些闪烁睿智之光的诗行,有不少又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启示。
将科学与诗歌有效地嫁接,让现代科技发散出耀眼的诗意光芒,这样的想法看上去很美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科技总是体现为一套残酷的物理法则,是一堆冷冰冰的东西,它与充满人文性与情感性的诗歌本身,往往很难统合在一起。同时,科技的原理表述与诗歌的情感诉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科技上所谓的“正确无误”与美学表达上的“正确无误”是完全不一致的。在《科学与诗》一文中,英国批评家瑞恰慈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文字的运用上,科学是与诗歌相反的,他认为:“在逻辑上与在科学上所用的语言,不能用来描写一片风景或一付面孔。”而诗歌的所谓正确性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因为神情,声调,节奏,韵律,在我们的兴趣上发生作用,并且使兴趣由无数的可能中选出它所需要的确切而又特别的思想,这就是诗的描写仿佛常常比散文的描写更正确的缘故。”也就是说,要想将现代科技巧妙化入现代诗中,不只是要做到遵从现代科技的客观事实,还要做到能将这种科技加以适切的人文转换,不仅捕捉到现代科技与人类生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还要将自己对于科技的人文性思考通过富有艺术性的“神情,声调,节奏,韵律”等语言形式,形象地彰显出来。在现代科技的人文赋意上,耿相新是做得较为成功的,前述《暗物质》《“算法”》《宇宙墙》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我们还可以《非理性》一诗为例来说明,全诗为:“那些真实的,挎着胳膊的/亲密的距离,听凭她非信任的/第六感,不朽的直觉,让她的冷静/近乎理性,悲剧从喜剧开始/这场宿命的隆起,将她从,未愈合的/叹息里,挽救,或者羽化为/一场巨大的相遇,这个丰盛的幻象/将她托在牺牲的荣誉之上,不可自拔/她的打开是一无所知的理性的盛开/她的关闭是无所不知的理性流浪”。现代心理科学研究生命,人类的理性是受制于非理性的,这就是诗人在《秩序·原子》一诗中所说的“理性的根深扎于非理性”,对于这一心理现象,诗人拟借女性的爱情来进行形象演绎,女性在爱情面前,表面上看仿佛是理性追求个人幸福的结果,实际上非理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更大,而这种非理性,是人类心灵世界中一个隐秘的真实,人类个体无法把握,这就注定了爱情本身在喜剧中常蕴含悲剧的人文色彩。整体来看,这首诗在诗境的处理、节奏的把控、语言的运用上,都是较为成功的,是将现代科技转化为诗意言说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