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的《从师记》,让人们知道了一个学者如何在时代浪潮中接续中国国学研究的传统,并踌躇满志将它传承下去。从作者的性格和才气,不易猜出他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家,他对现实的思考、对人生的定位超出他的研究对象,富有生气。作者多少有些爱书癖,在他的学生的眼里,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读书,唯有读书,能让他忘掉疲惫和劳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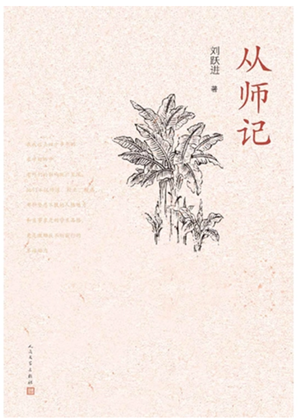
《从师记》 刘跃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立志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源于文学带给他的感动。在忧伤的岁月里,个人的命运随波逐流,作者接触到了文学。文学里,有一代人的迷惘、苦痛,也有绝望中的奋起和期待,文学对生命的热爱,与年轻学生积极的人生观契合。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罗宗强教导学生在历史背景之下掌握同时代学者的命运、选择,郝世峰加入个人自身经历的文学阐释,都让刘跃进着迷。归国学者叶嘉莹始终如一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以及教学中注入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真挚深沉的热爱,影响了这个年轻的学生。他下定决心,将古典文学研究作为终身学术追求。刘跃进在清华大学教书十年,他的讲课被做成视频资料公开发布。他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希望大学通识课一方面传授知识,另一方面培植同学们的爱国情感,在当代大学生中留下传统文化的根。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也要对社会有益,从历史走到现实,从现实反观历史,规划、解决人生课题。
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前辈给予他前行的力量。在现今中国学术的分类体系中,古典文献学专业最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学术和方法,同时,也是最早接纳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做自主的、独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担负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要求学生“存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具备普照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能力。学习这一专业,之所以要求学生有毅力、精神、气概,不外乎传统学术高山仰止,令人生畏,而在社会上不受重视,作者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时也遇到过这种状况。曹道衡和沈玉成两先生听闻年轻的学者对南朝五史的文献有自己的见解,觉得“空谷足音”,实在难得,倾心教授。姜亮夫、罗宗强、王达津、郭在贻、曹道衡、沈玉成这些身负绝学的老师,犹如“暗夜光明”的指路人,也是“吾道不孤”的同行者,是孤寂的学术生涯里的支撑。作者深情地说,老师是我前行的动力。他也经常以钱穆不仰慕追随时代潮流自励。除硕士、博士阶段的指导老师,在清华大学任职时拜访的各个学问满身的学者,也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跃进对古典文献近乎偏执地热爱,令他阅读积满尘灰的古籍时甘之如饴。文献学只是文学研究的基础,通过古典文献阅读,进而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做“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才是目的。姜亮夫先生教他将清华大学的学术传承下去。清华四大导师以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问,中西兼备,古今博通,在西方国家试图以西方文化掌控中国青年的未来的时代,清华导师不遗余力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代言。作者主张学习、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现状,建立宽广的学术视野,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建立本民族的文学观念。他教导学生从事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典章、职官、地理的研究,自己动手编辑资料,由目录学登堂入室,密切关注学科进展。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说:“人无痴者,无可与之交,因其无深情也;人无癖者,无可与之交,因其无真气也。”作者自年少时立下的学者梦,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因为热爱,所以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