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三个家庭:
第一家是16世纪爱尔兰农民凯利一家,拥有一小块土地,三个孩子(一儿两女),此外还有一个女儿,刚刚死肺炎。靠那块土地,勉强能养活全家。一次,凯利先生偶尔听说美洲传来一种新食物,叫土豆,产量比小麦高许多。凯利先生将信将疑,凯利夫人则主张冒险。
土豆果然带来大丰收,凯利家甚至可以将一部分土豆卖到集市上,赚到的钱用来翻新房屋、添置保暖衣物,凯利夫人又怀孕了……凯利夫妇从没想过送孩子去读书,种土豆不需要学习,新增收入只用来消费。他们的孩子依然耕种那小块土地,人口多了,又陷入贫穷中,直到1846年,爱尔兰土豆因病毒大幅减产,上百万人饿死,另一些人移民美国。
第二家是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农民工琼斯一家,他们也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在工业化冲击下,全家放弃小块农田,进城打工。工作累,但收入大大增加,琼斯先生拿出一笔钱,求纺织厂总技师收自己的大儿子为徒,这意味着,大儿子将来不用再干脏活累活了,二儿子有些沮丧,因为父母已没钱让自己拜师,他这辈子很难脱离车间。
第三个是20世纪早期瑞典渔夫奥尔森一家,夫妻都识字,他们通过关系,从银行中贷了一笔款,买了更大的渔船,他们也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收入增加了,便将孩子送到贵族学校,此前孩子们偶尔会打工,现在奥尔森夫妇要求他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得到高薪职位。
显然,凯利、琼斯、奥尔森都是人类,拥有同样聪明的心智,但他们的选择如此不同,清晰地标志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落差。
长期以来,当我们说到现代化时,指的是以发展为核心、工业化文明、科技进步、教育普及、观念改变……但美国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的这本《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则聚焦于另一个事实:通过现代化,人类的平均收入增加了14倍,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
我们常以为,进步来自“人的观念改变了”“技术进步了”,奥戴德·盖勒则坚信,这是倒因为果——是人的进步带动了观念的进步、技术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在漫长的人类史中,发展一直是主题,否则初民不会放弃闲适的“游牧—采集”生活,转向农耕,也不会从游群到部落,从部落到酋邦,从酋邦到国家。只是近代之前,人类的发展梦常受制于“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是几何级数的,财富增长是算数级数的,后者永远无法追上前者,最终,人口增长不仅会吞噬所有财富增长,还会引发人类社会阵发性的动荡。
关于几何级数增长,最著名的案例大概是:
湖中浮萍每天增长一倍,30天后将覆盖整个湖面,将湖中的鱼全部闷死。可直到第29天时,鱼们都没有意识到危险——此时浮萍只占湖面的50%,看上去很安全。
“增长—人口增加—资源紧张—崩溃—大量人口死亡—再增长”成为重复数千年的死循环。
据估计,3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日均工资约7公斤小麦,到工业革命前夜,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10公斤小麦,法国的巴黎是5公斤,意大利的相关城市是3—4公斤。三千年间,个人收入几乎未涨。
从距今4000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的遗骸推断,当时人均寿命30—35岁,而工业化时期的法国、瑞典、芬兰也基本如此。
显然,所谓现代化,本质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克服。但直到今天,学者也找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来标注人类是何时克服的,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财富的发展,转化为个人的发展。
马克思曾预言共产主义革命的爆发,但它率先发生在俄罗斯,那里8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未发生类似变化。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为防止利润率下降,资本更多投向人力资本,导致人力资本的价格猛增,引发大众教育革命,从而缓解了资本与人之间的冲突。
为了获得高工资,人们加大了教育投入,女性不再愿意过多、过早生育,在100年间,英国女性从平均生育5个孩子降到了2.5,在“收入增加—投资个人—收入更多—消费能力上升”这一正反馈机制下,人口生产反而变成“数学级数”的速度增长,经济成了“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马尔萨斯陷阱”彻底失效。
在中国,不少人基于“现代性批评”,将现代化视为机器替代人、掌控人的过程。而本书则呈现出更乐观的图景:现代性的最大受益者是人,人始终处于现代性的核心地位。
工业化初期,一度童工泛滥,留下“资本吃人”的刻板印象,各国纷纷出台法律,但从事实看,这些法律作用甚微,直到通用性技术普及,工厂不再需要低技能的童工,童工现象才大幅减少——表面看,这是政府功劳,但事实上,童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存在,是发展使其消亡。
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常执着于更多的生产、观念更新、以增长为中心等,甚至不惜牺牲人来满足它们,但美国“锈带”的衰落留下深刻教训。在今天,以人为本的发展依然有效,只有个体在自我教育上更多投资,主动提升人力资本、改善命运,这才是走向富裕的王道。
事实是,遭遇“锈带”危机的美国更富裕了,而不是更穷了,在“脱实向虚”“空心化”等说辞的一叶障目背后,过去20年,美欧的个人收入持续增加,被欧美国家逐渐放弃的实体生产虽让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体量迅速做大,但在人均收入上,仍存较大差距,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内卷化甚至还拉大了差距,走向“干活越多,生活越穷”。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用“方案的力量”对抗“系统的力量”,背离现代化的整体走势,必然是“累死也无功”。
以历史上的英国为例,英国是最早跨越现代门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英国当年高速增长时,中国、印度等即将完成跨越的国家反而出现了倒退,一些国家甚至用了上百年,才又回到当初的水平。除列强掠夺、内部分裂外,本书揭示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英国通过工业化,率先实现了将“经济发展”转化为“人的发展”,通过倾销,英国工人更富裕,更愿投资自己,而其他国家为购买工业品,只能出口农产品,不得不将农民进一步锁死在土地上,只有“经济发展”,吞噬了“人的发展”,随着人口迅速增加,引发社会危机。
如今,现代化正逐渐摆脱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因为它的利润太低,对“人的发展”推动乏力,随着大量高学历、同质化人才涌现,社会进步并未加速,反而引发各种冲突。这提醒我们:应警惕对现代化理解的偏差,短期快速增长下,暗藏着长期风险,一旦形成集聚效应,局面将难以扭转,一切可能又会回到“大刀长矛战洋炮”的窘境中。
本书下编重点回应了“全球财富为什么不平等”之问,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议题:如果现代性具有通约性,则后发国家照抄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岂不速成,可为何很少能成功?
本书认为,迁移距离、地理、疾病、文化和政治制度五个因素同时影响了“财富不平等”。
所谓迁移距离,指人类皆出自东非,走得越远,基因多样性越低,越易形成凝聚力;至于地理,则山地、平原、海岛、沙漠等会塑造出不同文明形态,它们可能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高度发达的玛雅文明因高山阻隔,始终未发明出轮子,这决定了它后来的衰亡;至于疾病,“黑死病”曾杀死欧洲1/2—1/4的人口,疫情后,生产硬件没减少,人力资本腾贵,推动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迎来近代化曙光;文化的作用更明显,从美国移民的情况看,文化影响可能持续几代,善于合作、重视集体、尊重女性的文化传统更有利于财富增长;政治制度则体现为攫取性制度和开放型制度的区别,攫取性制度可在短时期内带来快速增长,但最终会因压抑个体成长,背离“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走向反现代化。
本书提出了量化模型:各国之间没有明确来源的繁荣程度差异中,大约1/4可归结为社会多元性;2/5可归结为地理因素;1/7可归结为疾病因素;1/5可归结为文化因素;1/10可归结为政治制度。
本书倒数第二章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具体讨论了多元化的困境:多元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可能带来各种冲突,不利于政治稳定。多元化议题难推进,在于我们误解了多元化,只从不同宗教、不同族裔、不同文化来评估,但事实上,同一族裔内部并非同质,其差异化甚至比不同族裔的差异化还高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多元化不是同一民族、同一信仰、同一文化就可解决的——最缺乏多元化的国家玻利维亚如有所改变,人均收入会增加5倍;最多元化的埃塞俄比亚有能有效控制,人均收入也可增加2倍。
本书作者作为“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试图给出一套能回答各方驳难、平衡诸家意见的整体性发展理论。在本书中,将人均收入视为增长的基本指标、将现代化视为对“马尔萨斯陷阱”的克服、将地理因素视为全球性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等,均引自其他学者的成果,这让本书看上去有点像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人类简史》中有许多推断性观点,本书则立足实证、言必有据,而本书后半部更是《人类简史》所未及。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还有特别的价值:作为长期徘徊在近代门槛上的古老民族,我们为实现跨越曾付出惨痛代价,终于对推动近现代历史运转的“巨大齿轮”有所认识,但这个认识仍有模糊性,从“全盘西化”到渲染传统,不乏夸张的立场切换,可能蒙蔽我们的眼睛——历史仍在延续,今天的价值要由明天来决定,一旦失去对变革的敏感性,忽略了“巨大齿轮”的异动,将一切解释成“别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就有可能剥蚀了我们的现实精神,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落败。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
历史在考验着这一代中国人,能否穿越表象去看问题,能否始终保持清醒、谦卑与理性。则《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这样的他山之石,便值得一读再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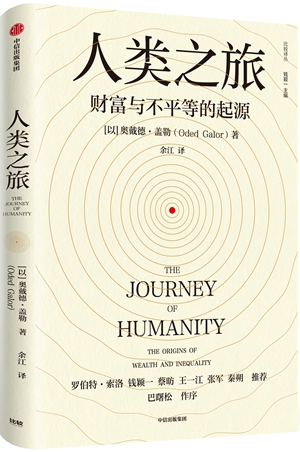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奥戴德·盖勒 著,中信出版集团
世界亿万生灵中,独有人类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人类的经济繁荣因何而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人口转型如何发生?全球发展水平又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古往今来,无数有识之士力图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尝试解答增长之谜的终极问题。
本书作者将利用独创的“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作者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各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
历史的影响深远悠长,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历史齿轮将继续运转,因地制宜地采纳合适的政策措施和价值观,将帮助实现人类的普遍繁荣。